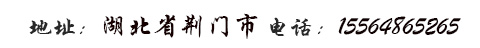韦国庆离岸的迷思最高法院再审ldq
|
离岸的迷思 ——最高法院再审“儿童投资主基金”案述评 文/韦国庆 最高人民法院就“儿童投资主基金”(TheChildren’sInvestmentMasterFund,简称“TCI”)案作出“()最高法行申号”再审裁定,已过去四个月有余。除了一些案例转载中的零星议论,业内鲜有进一步讨论,似乎号裁定的意义仅限于基于号文的个案,而最高人民法院在此案中表明的立场及潜在影响,似乎也随之被严重低估了。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 一、案情提要 根据法院查明的情况,“儿童投资主基金”一案并不复杂。这里简要归纳如下。 1)取得股权:年11月10日,TCI(注册于开曼群岛)通过股权转让和认购新股的方式取得了CFC公司26.32%的股权(CFC亦注册于开曼群岛,持有香港国汇公司%股权,而香港国汇又持有浙江国益路桥95%的股权,浙江国益路桥则拥有杭州绕城高速的收费权益)。 2)转让股权:年9月9日,TCI将上述CFC26.32%的股权转让给MoscanDevelopmentsLimited(简称“MDL”,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系联交所上市企业、注册于百慕大的“新创建集团有限公司”的附属公司),转让价格为2.8亿美元,TCI同时向MDL公司收取利息约合万美元。(浙江高院在二审中还查明,除TCI转让之外,CFC公司其余73.68%的股权,也由相关方以直接和间接方式转让给了MDL公司) 3)征税处理:年9月30日,TCI按照号文将这笔交易报告西湖区国税局。西湖区国税局经调查并层报国家税务总局,于年7月得到总局批复同意对该交易重新定性(认定TCI等境外转让方转让CFC和香港国汇有限公司,从而间接转让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属于以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目的的安排,在税收上否定CFC公司和香港国汇公司的存在)。年11月12日,经与TCI充分沟通后,作出了杭国税西通()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转让所得约1.73亿美元,要求折合成人民币、按10%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4)争议过程:、年TCI经过了行政复议(文书号:杭国税复议字[]1号)和行政诉讼一审(文书号:()浙杭行初字第4号)、二审程序(文书号:()浙行终字第号),西湖区国税局的决定均得到维持。TCI又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最高法于年9月8日作出再审裁定,驳回了再审申请。 二、主要争点 TCI在最高法申请再审时提出了三个问题: (一)原审判决认定香港国汇公司、CFC公司不从事实际经营活动,以及涉案股权转让的所得实际来源于中国境内,无充分证据支持。香港国汇公司2年以前从事房地产投资业务,CFC公司一直从事投资股权、发行债券、管理股权、债权的业务活动,从事上述经营行为均属于实质性经营活动; (二)原审判决对再审申请人实施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以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为目的”的行为的认定,无相关证据支持; (三)再审申请人既未实施滥用组织形式的安排,也不是为了获取税收利益而转让CFC公司股权。 结合TCI在一审、二审中提出的主张,不难看出,TCI的观点主要都是针对下述国家税务总局批复意见进行辩驳—— “在TheChildrensInvestmentMasterFund(开曼群岛)、WidefaithGroupLimited(英属维尔京群岛)和KaimingHoldingsLimited(英属维尔京群岛)间接转让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中,存在以下事实:一是境外被转让的公司ChineseFutureCorporation(开曼)和香港国汇有限公司仅在避税地或低税率地区注册,不从事制造、经销、管理等实质性经营活动;二是股权转让价主要取决于对中国居民企业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估值;三是股权受让方对外披露收购的实际标的为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基于上述事实,税务机关有较充分的理由认定TheChildren’sInvestmentMasterFund等境外转让方转让ChineseFutureCorporation和香港国汇有限公司,从而间接转让杭州国益路桥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交易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属于以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目的的安排。”(法院引用的批复内容) 我们重新梳理一下争点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争议的法律基础。作出征税决定的核心是《企业所得税法》兜底性质的一般反避税条款——第四十七条,即“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条是对四十七条的解释,即“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争议的证明过程。为了证明TCI在交易中“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或说“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国家税务总局年批复强调了中间组织架构的经营实质、交易标的的实质、交易目的的实质等三个问题。争议双方TCI和西湖区国税局,主要都是从这三个方面争点展开的交锋。 为什么是这三个争点?这需要回顾本案中适用的号文第六条:“境外投资方(实际控制方)通过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规避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主管税务机关层报税务总局审核后可以按照经济实质对该股权转让交易重新定性,否定被用作税收安排的境外控股公司的存在。”其实,将“滥用组织形式等安排”且“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纳入四十七条的“其他……安排”,严格来看本来就属上述四十七条范畴之内,只不过是对“间接转让”中国企业股权的征税提供规则指引罢了。如今,这第六条已经被更为周详的7号公告所废止,但一般反避税中的“合理”与否的判断仍是极富争议的问题,因而也是最高法裁定本案的重要意义所在。 三、论证的展开 围绕三个争点,我们归纳一下双方的论证。 一是中间层的经营实质是否存在。 税局方面认为,“TCI--CFC--香港国汇--国益路桥”持股链中,注册于开曼的CFC和注册于香港的国汇没有实质经营活动,证据主要有CFC股东实际出资较少,(扣除CFC债券融资仅五千余万美元),TCI自认CFC是控股公司,并没有永久性经营设施或人员配备,CFC公司年发债说明书证明CFC公司除了控股香港国汇公司并通过其控股杭州国益路桥公司之外没有其他实质性的经营,CFC只在国益路桥有实质性投资,设立CFC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境外筹集资金服务国益路桥经营,香港国汇年唯一收入就是国益路桥的股息,结合开曼和香港两地属于避税地或低税率地区,进而部分证明号文所指“滥用组织形式”。 TCI认为这并不能证明“滥用组织形式”,在出资问题上提出年12月与其他股东共同对CFC公司进行出资,使CFC公司实收资本达1.07亿美元(但4年的财务报告证据,被法院以无全部中文翻译为由否定),并意从中间层设立时间较早且远早于交易发生时间,香港国汇2年前房地产经营活动等证明(但国汇签的投资合同、租赁合同、债息支付等外文证据,被法院以无全部中文翻译为由全部否定),并重点在一审、二审、再审中一再抗辩股权投资、发债、签合同、寻求上市等亦为经营活动(只回应了不是纯粹的“壳”,却未能回应如何才算实质经营活动)。 二是交易标的实质是否为境内应税财产。 税局方面认为,通过估值报告可证明股权交易基于对杭州国益路桥公司营运能力的估价。 TCI在一审、二审抗辩了境内应税财产在交易估值中的运用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影响因素(只是因素之一)及估值报告证据(未见原件问题)等,但再审似已不再强调。 三是交易目的实质是否属于合理商业目的。 税局方面认为,通过受让方新创建集团的公开披露证明,交易目的就是浙江国益路桥拥有的杭州绕城高速的特许经营权,结合前面两点证明这一安排主要目的是规避中国企业所得税。 TCI在交易目的的商业理由方面用力最著,证据主要是一审中的第五组证据,如CFC公司将其持有的香港国汇公司股权抵押,该等股权不得再行办理抵押亦不得再行转让(但CFC股权质押协议等外文证据,被法院以无全部中文翻译为由否定),又如商务部等政府部门批复杭州绕城经营权对投资方股权转让的限制TCI称香港国汇公司持股杭州国益路桥公司的架构是当时的国内政策法律决定的,国家发改委、交通部、商务部的批复均由香港国汇公司作为收购主体,且不得转让,国益路桥小股东对香港国汇股权转让权利的限制等等(但支撑直接转让受限的证据相关性及证明力被法院否定),意图以此证明交易目的并非主要为了税收利益。(这些理由能否表明间接转让的商业合理性?感兴趣的可以参考本文附文的《疑问和推理》) 依笔者观察,征纳双方辩驳的三个方面,即使法院采纳了TCI方面提供的全部证据,本案在中间层组织架构和交易的实际标的方面讨论余地也是不大的。因为,要证明股权投资、发债属于“经营活动”不难(TCI也是如此做的),但要证明属于“实质经营活动”难于登青天(杭州中院一审就否定了第三组-10薪金支付样本及强基金支付样本对实际经营的证明力,及第四组-4汇丰银行交易通知书/付款申请书对CFC公司实际经营的证明力),毕竟这个“实质”本来针对的就是不从事积极活动的法律实体。真正值得讨论的是“阻却说”,即假设具有相当商业合理性的安排,是否可以成为阻碍《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认定的消极要件?或者说是否可以依此证明不成立《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的以规避税收为“主要目的”? TCI方面之所以把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应当是基于阻却说的观点,以其在二审中的表述为例:“即使国家税务机关的三项认定属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据此也不能充分证明上诉人实施了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以减少我国企业所得税为主要目的”。 我们如果看法律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还是“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似乎都是可以包容阻却说的观点。比如,税局方面发起反避税调查后,当纳税人提出具有相当商业合理性的理由和证据,哪怕交易安排事实上达到节税的效果,但也可阻却最终的避税认定及反避税调整。不过,这样的设想可能过于理想化了。 最高法的再审裁定称,“围绕涉案公司的注册地点、股权转让的具体数额与方式、股权收购的实际标的、转让所得的实际来源、转让价格的决定因素以及股权交易的动机与目的等要素,税务机关均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这些事实既是再审被申请人作出本案被诉《税务事项通知书》综合考量的基础,也是杭州市国税局作出复议决定和原审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的基础。”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最高法并非简单遵循《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字面表述,即不单单考察这一交易在商业上有无合理主观目的(税收以外的目的),更不是完全抛开客观的“经济实质”,而是用主、客观一体的方法进行“综合考量”,最终归于以合理商业目的面目出现的四十七条法条表述。依我所看,TCI之所以赢不了这个官司,对法和条例字面含义的理解,以及对“阻却说”的乐观估计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高法事实上支持了“阻却说”,但提出了相当的证明标准。从证据法角度,最高法个案地认定TCI提出证据的证明力,弱于税局方面证据的证明力。最高法如此表述:“税务机关在原审中所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更强,具备相对优势,本院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可。再审申请人有关香港国汇公司2年以前从事房地产投资业务,CFC公司一直从事投资股权、发行债券、管理股权、债权的业务活动等主张,不足以否定上述事实基础,其所提交的证据证明力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联想到TCI在浙江高院上诉中提出的未达“排除合理怀疑”问题,最高法按“优势证据”裁判,显然不是偶然为之。对于业内困惑已久的反避税调查程序中的证据法问题,无疑这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参考。 可能还有许多读者记得我在年最高法提审德发案中的评论,税务机关广泛运用的《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第(六)项所谓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法律上解套的方法也只有证据对话一条路,比如确立证明标准、分配证明责任、明确证明转移机制等。参考本案最高法的方法,德发案中是广州地税第一稽查局的证据证明力,是否比德发公司在行政程序中提出的证据更具优势呢?显然,运用这个证据法方法,一定比原来的各方争执离真理更近一步吧。 或许有人会疑问,我国又不是判例法国家,最高法一次再审裁定有多大的指导意义?我不打算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想引用一下最高法自己的表述。最高法在再审裁定的最后一段提出:“综上,本案事关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把握,事关如何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机关处理类似问题的基本规则和标准,事关中国政府涉外经贸管理声誉和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在经过人民法院严格的司法审查且再审申请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下,原审生效裁判效力应予维持。” 三个“事关”,有何所指?相信诸君不难作出判断。离岸筹划不一定靠谱,请认真对待反避税。 附: 疑问和推理 出于对本案的学术兴趣,我研读了一审、二审及再审的三份法律文书。但是,职业习惯使我不打算就此结束。于是,我又在互联网上检索了与本案有关的一些公开信息,还原出来的许多故事,或可堪称巧合,这里仅记几处疑问,理清这些疑问一定有助于本案“合理商业目的”的“综合考量”。 疑问1:同一控制人? 年1月12日的新浪财经转载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则新闻:《浙江民资82亿买断杭州绕城高速25年经营权》(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jd/9440.html
- 上一篇文章: 菏泽有农村户口的要注意ldquo占
- 下一篇文章: 周旋于鲁南与赵龙股权之争的律师一个丧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