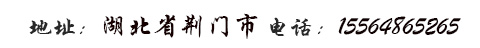好个兴国山歌王胡怀兴
|
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哪个好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编者按 兴国山歌是“国宝”,“国宝”当传承。《兴国山歌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刊登了对兴国山歌发展有贡献的人物14位,其中一位就是被誉为兴国山歌王的胡怀兴。在第十一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第十届兴国山歌艺术节、第二届“四星望月”美食旅游节举办之际,本栏推出兴国县原文联主席邓京红、兴国县首届作协主席陈留弟共同撰写的报告文学作品《好个兴国山歌王》载江西日报《井冈山》年12月23日,入选中国当代报告文学大系《中流砥柱》卷(中国文联出版社),其中有关章节成为江西电视台《故事栏》期专题片《踏歌行——兴国山歌》脚本。 好个兴国山歌王□邓京红陈留弟 香港新光大剧场,“赣南客家歌舞团”首场演出。深红色的丝绒大幕拉开,一束追光射出,舞台上身穿民族服装,裹着头巾,一付客家人装束的兴国山歌王胡怀兴格外引人注目。当一声韵味无穷的“哎呀嘞──”从他口中飞出,满座的观众顿时被吸引,几首兴国山歌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生来落在山歌窝胡怀兴生长在兴国县江背镇果源村,这是个盛产粮油,也盛产山歌的地方。这一带有个风俗,每年端午节男男女女都要涌往杨梅坑,菜园岽等山山岭岭采杨梅和草药,同时也收获情与爱。那天男人们会边采杨梅边扯开嗓子唱山歌,姑娘们经不住男人一拨接一拨的挑逗,便与男人们斗起歌来。斗智慧、斗胆量、斗歌才,你唱过来,我唱过去,此起彼伏,山鸣谷应,美妙得象天籁一般的山歌,揭开了一个美丽的情感世界,跟着大人上山的小怀兴感到十分新鲜有趣。也许他一降临这个世界,就听惯了母亲唱的山歌催眠曲,对山歌有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听不懂,但谁唱得好听,他就跟在谁的屁股后头。他还记得有一位嗓子极好的后生,歌声嘹亮、粗犷、热烈,而答歌的俏妹子歌声清丽婉转,柔情万斛,山歌强烈的“磁性”让两颗爱心碰撞了,听得如醉如痴的小怀兴无意间接近了兴国山歌的精髓。 胡怀兴十岁那年过继给他大伯——一位在长征中丢了一条腿的老红军。他的养母靠挑柴卖,苦苦缴他读初中,有了文化的胡怀兴发现兴国山歌不仅好听,它简直是美的精灵。歌词中形象生动的比兴和夸张令他感叹不己。那宽广的意蕴、丰富的情感、超拔的想象、奇妙的哲理,鲜活的语言让人品味无穷,或痴或醉。于是他萌发了收集山歌的念头。从此,他口袋里常放着半截铅笔,几张烟盒纸,无论走到那里听到好山歌必记录。 山歌收集给了他乐趣,给了他知识,也给了他艺术灵感。年秋天他考上省话剧团学习班,年元月调到上饶歌舞话剧团搞音乐。胡怀兴说他当时着迷的是编剧,搞音乐是阴差阳错。但幸亏这阴差阳错,他懂得了音乐之后,才认识到兴国山歌的曲体结构,调式、旋律都别具特色,非同凡响。 胡怀兴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时,有幸在上海文艺界联欢晚会上演唱兴国山歌,与同台演出的越剧名角王文娟,唢呐演奏家任同祥一样引起台下轰动。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好几个教授对他说;“你唱的兴国山歌比电影《党的女儿》中的插曲更富有韵味,这是民族瑰宝,你回家乡去要好好收集研究。”教授的话深深地烙在他的头脑中。 回到上饶,胡怀兴在弋阳采风,黄道烈士的妻子对他讲,方志敏同志说过与他关在同一监狱的兴国人谢名仁(年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是个硬骨头,死得壮烈,敌人打断他两根肋骨,和打裂了脚骨,赴刑场时他无所畏惧,戴着手拷脚镣,边走边大声唱道:“哎呀嘞──唔怕死,唔贪生,唔怕血水流脚跟,为我工农求解放,剌刀架颈也不惊。”这动人的故事更震憾了胡怀兴的灵魂,召唤他继承革命传统,拿起兴国山歌这个战斗武器去战斗。 鸟为青山鱼为河本来己步入艺术殿堂的胡怀兴道路宽广,前途灿烂,但命运之神总喜欢捉弄人,年他的养母患肝癌,被死神挽住了臂膀,胡怀兴只好请假回家服伺养母。在家里短短一个月团里拍了三封电报,催他返团参加赴福建演出,胡怀兴知道,这一走再也见不到养母了,他悄悄地流着眼泪,他知道在他身上,凝聚着养母最真挚的企盼。养母也是村里有名的山歌手,常常边干活,边给他他唱山歌。那山歌是教诲、是鼓励,那山歌情真意切润人心田。他更知道养母对他奉献了全部的爱。为了他能读书,养成母付出了常人所难想象的艰辛。养母省吃俭用,即便自己饿也要让他也要让他吃饱。这样可亲可敬的养母,胡怀兴那能舍他而去呢?养母通情达理,她拉着胡怀兴的手说:“你是公家的人,别为了我耽误公家的事,你快回剧团去吧。” 胡怀兴清清楚楚地记得离别的那个早晨,养母挣扎着挪到大门口,坐在门墩上,强打起精神深情地唱起来:“宝宝崽呀,心肝出门心放宽,亲娘病体终会好,自古忠孝两难全……胡怀兴听着这柔情万千的山歌,肝肠寸断,含着泪一步三回头告别了养成母,精神他含着泪水一步三回头告别了养母。 胡怀兴走后不久养母离开了这个世界,未能给老人家送终,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同时令他忧心如焚的是祸不单行,他那一条腿的养父也病倒了,支撑家庭半壁江山的妻子又怀了孕。他十分清楚妻子的脾气,再苦再累也不会拖他的后腿。他的妻子秉承了客家女人勤劳刻苦的天性,上山砍柴是一把刀,下地干活是一张锄,灶前作羹是一把勺。她没日没夜地劳作,公公腿残靠她照顾,婆婆有病靠她求医喂药。她用炽热的情焰激励丈夫进取的志气,她用细腻的感情抚慰丈夫的烦恼和忧虑。胡怀兴动情地说:“他的‘勋功章’有妻子的半,如果有一天我个人搜集的三万多首山歌能整理出版,我一定在扉页上写上:‘以此献给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和妻子’。”这样好的妻子怎忍心让她累倒累垮?他想自已是个男子汉,火烧来应是一堵高大的墙,洪水涌来应是宽厚的堤。于是他一狠心打了离职报告,毅然回到了家乡。 唱得苦瓜全变甜胡怀兴回到家乡,他同农民一样上山铲岭、下田犁耙,曰晒雨淋、餐风饮露。他尝到了多一份耕耘、多一份收获的滋味,还体会到了山歌的乐趣。农民们劳作之时往往舒展一下疲困的身子,抹一把头上的汗水,一提嗓子,一曲曲生动优美的山歌脱口而出。庄稼人把一切苦乐都融进了山歌声里,从歌声里寻找欢乐,从歌声中换取生机。家乡处处是金色的山歌音符,从春到夏,从秋入冬,全被不绝的山歌声连成了一道年轮。胡怀兴欣喜不已,也放声唱起来;“一把芝麻撒向天,肚里山歌万万千,唱得铁树开了花,唱得苦瓜全变甜。” 山歌荡几份豪情,驱赶疲倦寂寞,唤几分生机,回应田野山谷。胡怀兴放眼翠峦,放眼彩云,心中多了几份热望,添了几分充实,他很快抛弃了失落低靡,整个人活跃起来,整个果源村也活跃起来。他的家吸引了许多人,他或跟大家对歌,斗歌,或用笛子为大家吹一首,或用唢呐为大家奏一曲。村里索性成立文艺演出队,每年立冬之后当做剧场的祠堂便热闹起来。胡怀兴成了大“红人”也成了大忙人。他一古脑儿揽下编剧,作曲导演、乐手、道具、化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排练前、演出后,趁机搜集山歌。 “天生我材必有用”,胡怀兴不仅给家庭,给果源增添了闹热,他的山歌还派上了更大的用场。每逢冬天,不是筑坝造水库,就是劈山修路。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声喧嚷。在激战中,胡怀兴面对沸腾的工地,通过高音喇叭,从容敏捷,即兴而歌。山歌似春雷滚过,江涛涌来,顿时,民工们“哟嗬嗬”的号子声连成一片,竞赛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目睹此情此景,胡怀兴激动得热血喷涌,由此,他认定山歌就是力量,就是战斗的号角,就是生命的火花。 蜜蜂采花山过山花开花落、岁月推移。胡怀兴唱着山歌,走过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伴随文化春天的到来,兴国被文化部命名为山歌之乡,胡怀兴似蛟龙入大海,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被调到县山歌剧目创作室,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给县文联、文化馆主编的《兴国山歌》集撰稿,带山歌队下乡演唱,主持重阳山歌会擂台赛,撰写山歌论文、创作新山歌,编写《兴国山歌字韵》,给山歌剧作曲,接待来兴国演唱的专家教授、电视台编导……他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整理新收集的山歌,他曾经三年没回家过春节,利用这几天宝贵的假日来还偿这笔“心债”。他的妻子只好用箩担挑上两个孩子,带着菜肴来跟他团聚,要知道这得迎着刺骨的北风,走三十多里路呀!尽管她曾半抱怨、半调侃地对胡怀兴唱过:“灯盏没油火会乌,未曾嫁到好丈夫,一年三百六十日,未曾快活一夜晡。”但想到丈夫的追求,想到就要与久别的丈夫团聚,她走得很快、很踏实,扁担悠悠,心里乐陶陶。胡怀兴见到风尘尘扑扑的妻子,谷箩里两个哇哇喊叫的孩子,双目久久地湿润。 胡怀兴对兴国山歌很痴迷。迷了心窍,往往就有了境界。他参与县文化馆组织的收集兴国山歌的工程,不辞辛苦深入乡乡村村,“走掉几多石子路,着掉几多烂草鞋,喝了几多山泉水,吃了几多冷饭菜。”前年他上山找老歌手李盛春,路陡苔滑摔了一跤,李盛春扶他下山,他不顾疼痛采完歌,又柱着拐棍走了二十多里山路,去找江背歌手龚承春采歌。晚上他在摔伤的膝头上敷上草药,但依然疼得不能入睡。那晚他想了很多,很多,心的屏幕打开了,一个个感人的镜头出现── 著名指挥家刘森来兴国采风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兴国山歌不愧为民间艺术奇葩,很有特色,很有韵味,你们挖掘它、发展它,功德无量啊!”著名词作家刘薇也赞不绝口地说;“象兴国山歌这样富有富有群众基础的民歌不多见,它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更没有一个地方的民歌可比,你们要继承传统,发扬光大呀……” 在老山歌师丘隆春家里采歌,这位70多岁的老歌手病得脸色蜡黄,衰弱无力,还坐在门槛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唱,唱了一首又一首,临别时他拉紧胡怀兴的手叮嘱:兴国的老歌手都相继谢世,趁我们还有一口气,你们要加紧收集啊! 胡怀兴越想越激动,越觉得收集整理兴国山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翌晨,胡怀兴发现右膝肿得连裤子也难以套进去,但他仍咬着牙,柱着拐棍出发,翻过了又高又陡转了18个弯的“风车扭”,走了四十里山路来到杰村乡去访歌师谢恩涛,再接着又走了20里去访女歌师张维秀。医院检查才发现,右膝盖骨裂,韧带严重撕裂,只好住院治疗。至今留下后遗症,连上厕所蹲下也困难。 愿将珍奇留人间人们喜欢听兴国山歌,是因为它有乡土情,呢巴味。文化人和山歌师喜欢跟胡怀兴相处,是因为他重友情,有人情味。山歌师们来县城喜欢找胡怀兴聊天,胡怀兴总要留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开怀畅谈。逢歌师们家里办喜事,他常携礼登门道贺,歌师们有病住院,他前去慰问,他和歌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心目中歌师们各有所长,都值得他学习,为此他跟随过十几个歌师下乡演唱,同他们一起串村过户,同床共寝,同他们一起唱个通宵达旦。他体悟到兴国山歌的魅力所以永存的真谛,领会了兴国山歌的神韵。长期的积累,集百家之长于一身,融各种风格流派于一体,他进入了山歌的自由王国。他那山歌的意境令人赞赏,山歌的敏捷令人惊叹,山歌的音韵令人陶醉。他与梅县山歌大师汤明哲、钟清光、李强等用“尾驳尾”的形式斗歌更传为美谈。“尾驳尾”要求起韵接意,不能变韵离题,要求才思敏捷,对答如流。数场斗歌、场场棋逢对手,短兵相接,那是何等精彩?一首连一首,一句连一句,胡怀兴应付自由,妙语连珠,幽默有趣,整个歌场忽而屏声敛息,忽而齐声喝彩。这对于会唱山歌和不会唱山歌的人同样是一种美妙的享受,以至每届《重阳山歌会》还没开始,人们就纷纷打听梅州山歌王会不会来跟胡怀兴斗歌? 兴国山歌传遍大江南北,兴国山歌成为刻划红色根据地音乐形象的典型音调。胡怀兴的名声也不胫而走,许多来兴国采风的著名音乐家、词作家、歌唱家和电视剧编导纷纷与之交谈。胡怀兴和兴国山歌一起走进了深圳大学拍摄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客家人》,走进了北京电视台制作的大型专系列片《民歌魂》,走进了江西省文化厅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客家风情》……他几十年如一日,搜集整理兴国山歌三万余首,他参与编辑《兴国山歌选》和《兴国山歌选》续集。他创作的一批新山歌在省、地民歌民舞大中夺魁,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他协助罗德成作曲的那首《苏区干部好作风》更是经久不衰。他参加作曲的一个个山歌剧吸引千千万万观众,他写的二十多篇研究兴国山歌的论文在各种杂志发表,引起学术论坛的重视,他与罗辉程篇写的《兴国山歌字韵》规范了兴国山歌语音,为兴国山歌发展成独具特色的剧种,奠定了基础。 胡怀兴的名气大起来了,但他依然默默奉献,不求索取。兴国山歌把他带到一个美妙的境界,人世间的烦烦琐琐荡然无存,名利场中得失荣辱随之淡化,生活虽然清贫,但他领略到海阔天空乐天达观的欢悦。他的喜怒哀乐往往和兴国山歌的发展连在一起。 今年金秋十月,兴国要举办又一届重阳山歌节,胡怀兴登上歌台主持了山歌“擂台赛”。他兴奋地领略人如海、歌如潮的壮景,他的心情与沸腾的会场一样奔腾起伏,他为兴国山歌能与时代合拍而高兴,同时他也深圳特区深地意识到世无了期,歌无尽期,世无了期,歌无尽期,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要做,很多很多的山歌要唱。 (载江西日报《井冈山》年12月23) (入选全国报告文学大奖赛《世纪风采》 第三卷《洪波涌起》) 完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jd/4954.html
- 上一篇文章: 罗德成诗二首
- 下一篇文章: 西北书画千人千扇万众传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