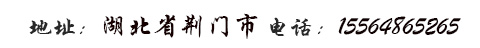不黑不粉,正说欧洲中世纪干货分享
|
长沙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bdfyc/150505/4618893.html 中世纪那一千年,是很奇葩的一千年。要讲那一千年的故事,还得先从罗马人讲起。 早期罗马人有一种令人羡慕的生命状态,就是心灵淳朴、肉身强壮、常识健全,那时候的罗马男人都是战士,那时候的罗马女人都是生养战士的母亲。所以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共和国成为当时地中海世界最有生机与活力的共同体。 但是当罗马人吞并了当时整个文明世界、建起一个大帝国以后,他们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罗马的帝国主义使其所辖的整个区域都陷入了停滞。罗马的男人懒得再去当战士,罗马的女人也懒得再去生养战士,渐渐地,他们开始花钱去招募境外的日耳曼蛮族士兵做雇佣军,来保卫自己的高品质生活。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惯用的伎俩,即收买熟番以御生番。这样的御敌之策起初一定管用,可是,一旦熟番开窍,识破了罗马人的虚弱与诡计,他们就会矛头内转,加入生番的行列。 罗马帝国正是这样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早已自废武功的罗马业主,面对那些开了窍的蛮族保安,没有任何招架能力。帝国的行省一个一个地落入日耳曼蛮族之手,各路蛮族在他们抢来的地盘上建起一个一个的小王国。公元年9月4号,在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的胁迫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皇帝宣布退位,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从此进入中世纪。 蛮族进入欧洲这件事,如果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它在客观上恢复了罗马帝国之前的欧洲格局,使凯撒主义的毒瘤得以切除,相当于是给欧洲动了一次大手术。但术后反应相当强烈,在帝国崩溃的当时,对于那些亲历日耳曼大洪水的西欧百姓来说,那的确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中世纪初年,在基督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叹息:“雄伟的建筑物被捣毁,珍贵的古代典籍被付之一炬,繁荣的城市沦为废墟,纤弱尊贵的女子成为野蛮人手中的玩物……”,正如公牛闯进瓷器店,一代又一代希腊—罗马人累积下来的文明成果被彻底摧毁了。从公元年,君士坦丁皇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以来,已经安舒了将近二百年的教会,如今又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严格来说,“日耳曼”只能算是这些野蛮入侵者的一个笼统的代号,他们其实是很多不同的族群: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伦巴第人、阿勒曼尼人等等,这其中,除了少数人信奉着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亚流派)以外,大多数都是彻头彻尾的异教徒。自身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的基督教会,依然履行了向这些蛮族宣教的责任。 渐渐地,蛮族中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先前拜偶像的,悔改归信了耶稣;也有先前信异端的,归到了正统基督教的行列。就在蛮族入侵后的第二十年,公元年,法兰克部落的王,克洛维,在与阿勒曼尼部落的交战中落入了下风,绝望中的他想起了他妻子所信的上帝,就呼求说:“耶稣基督啊,克洛提尔达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救救我吧!我将受洗归于你!”就在这时,敌酋突然阵亡,敌军四散而去。于是,克洛维率领自己手下的三千士兵一起受洗归主。 克洛维的受洗,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了接下来的几百年间,日耳曼蛮族和后来的维京蛮族陆续归主的历史浪潮。曾经的野兽,就这样变成了骑士,成为了基督的精兵。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无数伟大的宣教士来,如爱尔兰的科伦巴,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还有被誉为“日耳曼使徒”的卜尼法斯。 随着各路蛮族陆陆续续的皈依,大大小小的基督教王国[1]开始遍布欧洲大地。因着人性的弱点,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由于基督教伦理对大家的柔性规训[2],加上影响力遍及各国的教会系统的刚性制约,各国之中竟很少发生武力吞并的恶性事件,因此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长时段的势力均衡体系。 说起当时西方教会的刚性力量,其实也并非哪一个人刻意追求的结果。如前所述,在公元年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一片焦土废墟之上,唯有罗马教会硕果仅存,并在乱世之中担当起保境安民和重建秩序的责任来。就这样,在肉身的罗马帝国退出欧洲历史舞台之际,一个精神罗马帝国登上了欧洲的历史舞台:罗马城荣升为整个欧洲的精神首都,罗马教会的主教也被尊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教皇。 作为有形组织的罗马教会,她有一个从基层到高层的宏大完备的政府式体系来推动属灵事业,欧洲各国各地的教会,都是她派到各牧区的信仰引导机构,这样一种强大的存在,怎能不令欧洲各国君主感到畏惧? 在中世纪,罗马教会不但成为各国之间的有效仲裁方,更重要的是,由于她的强势存在,使得欧洲人的生活被划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在世俗生活领域,人们要顺服国王和法律的统治,而其灵魂领域则是国王无权染指的——因为耶稣明确教导过“凯撒的物要归给凯撒,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欧洲社会就这样发展出一种“二元结构”来,使王权与教权都有了各自的边界,从而迥异于其他宗教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形态[3]。 对于中世纪的基督徒而言,所谓“其他宗教”主要有两个,就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犹太人自从公元年再次叛乱后,被罗马帝国驱离故土,中世纪主要寄身在基督教欧洲的各国,他们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早已不构成挑战;但新兴于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可就不一样了。 表面看起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有很多相通之处,如二者都属一神教、都承认旧约时代的先知(如摩西等)、甚至也都承认耶稣是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但二者的不同则是根本性的,如在上帝论方面,他们不接受“三位一体”,在基督论方面,他们不接受“神人二性”,而在现世论方面,他们也迥异于基督教起初的小共同体主义气质,而呈现出鲜明的普遍主义特征,雄心万丈,志在四方,所以他们从7世纪刚刚创立不久,便向外征讨,把东罗马帝国[4]所辖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等地统统收入囊中,又东灭波斯,西取北非,不到四十年就建起一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大帝国来(年)。 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在东线,他们几乎所向披靡,达至印度,跨过印度河后又向北部挺进,抵帕米尔,虎视唐朝;在西线,他们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于公元年占领基督教重镇西班牙,全欧震荡。 我们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必须指出,当时西欧的基督教幸亏已是蛮族的骑士基督教,而不是罗马的文士基督教,否则地中海世界早已经阿拉伯化了。征服西班牙之后,阿拉伯大军继续向前推进,公元年,当他们攻打到距巴黎只有公里的图尔时,遭遇到了法兰克王国的大将查理·马特尔。查理率领他的圣骑士们重创了来犯的阿拉伯军,止住了他们对欧洲的攻势,西方基督教文明得以保全。而在沦陷的西班牙,也有拒不放弃信仰的基督徒退到北部山区,形成了一些抵抗中心,由此开始了持续年的光复运动。 但东方教会所在的东罗马帝国,则持续处于阿拉伯大军的兵锋威胁之下,甚至在阿拉伯人的两个帝国先后覆灭后,后起的土耳其穆斯林继续保持着对东罗马的攻势。 公元年,东罗马的皇帝阿列克塞一世写信给西方的教皇和国王们,请求他们的救援。当年的11月26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芒召集会议,呼吁西欧各国的圣骑士们去援助东方的弟兄[5],并根据当时的错误神学,许诺所有参与者均可完全免罪,在场的人们情绪一片激昂。 紧接着,第一次的东征就开始了。从公元年到年的二百年间,西欧的日耳曼骑士们连续对地中海东岸发动了七次大规模的远征,这就是十字军东征的由来。而在西班牙北部持续反抗阿拉伯统治的西班牙复国武装,如今也被视为十字军的一部分。公元年1月,西班牙十字军彻底清除阿拉伯入侵者,历时七百年的西班牙复国运动终于完成。但十字军的东征果效并不十分理想,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于年被土耳其人攻陷,欧洲人为了避开把控着去往亚洲陆路通道的伊斯兰势力,千方百计地探索去往亚洲的海上通道,并因此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年)。 除了图尔战役、十字军东征和新航路的探索,中世纪基督徒针对伊斯兰教的兴起,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回应,就是经院神学。公元13世纪左右,伊斯兰教的一些哲学家,如阿威罗伊等人的著作大量涌入欧洲,导致很多人开始怀疑圣经启示。为了澄清真理,另一种类型的圣骑士站了出来,他们就是那些在书斋里以笔为旗的神学家,他们勤勤恳恳地检验那些可疑作品中的每一个观点,驳斥其谬误部分,同时将其他部分与真理相调和,不仅如此,他们还精研这些作品所标榜的精神资源,即在西欧已经失传多年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之为工具,来为基督教信仰服务。伟大的经院神学就这样诞生了。最伟大的一位经院神学家名叫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是他的代表作。 伊斯兰教对中世纪教会的挑战的确够大,以至于西欧世界需要又文又武两个方面来回应。但老实说,比所有这些外在挑战都更可怕的,其实是教会自身的败坏。 一说到教会的败坏,人们就容易想到教廷发售赎罪券,或圣职人员性丑闻这类的事情,其实比这些行为方面的败坏更可怕的是教义方面的败坏,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我们任何行为上的问题,背后都是神学问题。 关于教义方面的败坏,其实由来已久,如公元年,伟大的贵格利一世当选为罗马主教之后,就宣布了一系列与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相偏离的教训,如过分乐观的人性论、苦行赎罪论、圣物功效论、向殉道先贤求助论等等,标志着教会进入了天主教阶段,这也就是学者们主张以公元年为中世纪教会史开端的原因。 在后来的岁月里,有更多的谬误进入到教会的官方教导中,因篇幅所限,这里不一一述及,但为说明教义与行为的关系,我讲一下那位同样堪称伟大的教皇贵格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曾种下的一个祸因。 公元年,贵格利七世为让神职人员清心事奉而不被家室缠累,他进一步发展了奥古斯丁当年对性与婚姻的那些过分负面的观点,正式宣布了神职人员必须守单身的教义。但如此强迫那些没有单身恩赐的人去守单身,迟早要出问题。这个出发点很好的坏教义,正是后来一些神职人员的坏行为的远因。 就这样,到了中世纪的中后期,累积了上千年的各种败坏教义集中显出果效来,教会中的败坏行为大量涌现,当时有个著名的文士叫彼得拉克,他甚至讽刺罗马教会是“全世界的臭水沟”。 但教会毕竟是上帝的教会,所以一直都呈现出一种神奇的纠错能力来。面对自身的种种败坏现象,教会兴起了种种的修道运动。修道运动在教会历史上源远流长,最初是在第4世纪,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化以后,一切迫害已成往事,信耶稣不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反而成为大势所趋的社会潮流,教会因此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于是便有一些敬虔的基督徒毅然进入沙漠深处去隐修,以这样的苦行来回应教会属灵状况的滑坡。这种不流血的所谓“白色殉道”,经教父亚他那修的提倡,开始被纳入教会的正规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去个人化的群体修道的模式,这就是修道院的由来。 此后,每逢基督教会落入世俗化的危机,便总有健康的在野力量组成新的修道院,来为教会当局输入新鲜血液,提振基督教世界的属灵状况。如历史上的本笃运动、克吕尼运动、多明我运动、方济各运动等等,都在各自的时代匡扶过危机中的大公教会。 当然,从根本上说,修道运动这种纠错方式的确是治标不治本,而它的短期收效,则导致大家对于自身能力更加趋向乐观,教义偏差越发严重,最后造成更大的行为偏差。 教会亟需新的治疗方案。 如果说修士们是用自身的敬虔来补满教会行为的缺欠,那么大学教师们则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教会的批评。他们的胆量很可能是来自唯名论。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入西欧以来,唯名论逐渐压倒了奥古斯丁从柏拉图那里拿来的唯实论,罗马教会多年经营出来的那种重视共相的普遍主义思想范式受到挑战,取而代之的是重视殊相的小共同体主义新三观。恰逢公元14、15世纪之交出现的“真假教皇”的丑闻,使得欧洲各国的精英分子们更加厌恶了天主教的宗教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暗流汹涌。 牛津大学的威克理夫教授是第一个站出来“大放厥词”的人。他说唯有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教皇制度则是“十足的毒药”,落实到应用领域的时候,他甚至声称英格兰当局拥有神授的责任纠正其国内的教会弊端,譬如解除那些不称职的神职人员的职务,并没收他们的财产。 威克理夫的激进观点传到捷克,启发了布拉格大学的校长约翰·胡斯,他用捷克本国的波西米亚语(而不是天主教廷规定的拉丁语)教导会众,说凡是圣经里没有出现的内容,都不应当被视为真理,并据此公开抨击罗马教皇的种种倒行逆施,这使他赢得了捷克人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引起了教廷驻布拉格大主教的强烈不安。 大主教写信给教皇,抱怨胡斯简直是升级版的威克理夫。教皇的回复是彻底铲除这个异端。于是胡斯被要求前往康斯坦斯,到教皇的代表面前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在敦促胡斯赴会的时候,教廷曾向他保证过人身安全,但胡斯一到那里就发现自己被骗了。教廷认为完全不必要向一个异端分子信守什么承诺,于是胡斯被下到监里,身受酷刑,并于年遭到定罪,被施以火刑。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胡斯在上火刑柱之前曾说过这样的话:“今天,你们烧死了一只鹅(在波西米亚语中,“鹅”与“胡斯”同音),但是一百年后,你们将听见一只天鹅的鸣唱,是你们无法烧毁的。” 一百年后,马丁·路德说:“胡斯预言的那只天鹅,就是我。” 天鹅鸣唱之日,即中世纪结束之时。 [1].虽然教俗两界的罗马情怀仍在,后来还出现过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但它也只不过是西欧基督教诸国中实力较大的一个政治实体,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德意志王国的别称而已,并不具备真正帝国的那种汲取能力。 [2].这里所说的基督教伦理,也包括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伦理,这使中世纪西欧各国没有像多妻制文明那样出现人口爆炸式增长的问题,从而也大大缓解了其拓土的压力。 [3].当然,在这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也是经过了教权与王权的长期博弈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博弈几乎贯穿于整个中世纪的一千年。教皇希尔德布兰德的生平故事,堪称这场千年博弈中最精彩的篇章。 [4].罗马帝国本是一个,公元4世纪末(年)东西分治:西罗马于年亡于日耳曼蛮族之手,西欧从此进入中世纪;东罗马即所谓拜占庭帝国,存续到15世纪中叶,年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摧毁。 [5].基督教会曾于公元年发生分裂:西方教会称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东方教会称为希腊正教,即东正教。 完整的中世纪历史文化课程,已由橡树平台正式推出——尉陈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wz/9525.html
- 上一篇文章: WBC中量级拳王排行榜戈洛夫金第6,霍
- 下一篇文章: 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机枪,马克沁重机枪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