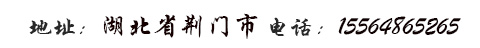尼罗河畔的飞扬与落寞尉陈讲建筑故事
|
在黄沙滚滚的北非大漠中,流淌着一条长达六千六百多公里的大河,号为“尼罗”。尼罗河源自维多利亚湖,蜿蜒北上流入地中海,途中经过六个急流险滩后注入狭长的河谷,然后呈扇形展开,漫流于河口的沼泽低地上。这一河谷及河口地区,由于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变得异常肥沃,庄稼竟可一年三熟。据希罗多德记载:“那里的农夫只需等待河水自行泛滥,流到田地上灌溉,灌溉后再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田里,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以后便只需等待收获了。”当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尚徘徊于蒙昧蛮荒之中时,这里的百姓便已率先迈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聚合成一个名叫“埃及”的富庶国度,因此古埃及文明曾一度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 早在公元前年,也就是距今多年前,尼罗河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古老的埃及王国,它的国王被尊称为“法老”(该词原意为“高大建筑”,后来逐渐演变成高大建筑拥有者的特定称谓)[1]。法老权力很大,他们头戴红冠,以眼镜蛇为守护神,蜜蜂为国徽,这就是所谓的“下埃及王国”。后来在尼罗河的上游(即南部河谷地带)又形成了一个国家,史称“上埃及王国”。上埃及的法老服色尚白,崇奉鹰神荷鲁斯,以苏特树为国徽。因着人性的弱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上、下埃及皆欲除灭对方而成一统之业,但二者势均力敌,故在数百年的浴血相争中始终处于拉锯的平衡状态。直到公元前年左右,亦即距今多年前,头戴白冠的“终结者”美尼斯(Menes)挥师占领了下埃及,从此上下埃及被合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专制大一统帝国[2]。美尼斯在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的交界处(今埃及首都开罗附近)营建了一座新的首都——白城,即后来希腊人口中的孟菲斯。埃及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自从古埃及被帝国化以后,它的历史分期大致是这样: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为早王朝时期(第1~2王朝),建筑以长方形的“马斯塔巴”贵族墓为主;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为古王国时期(第3~6王朝),建筑以金字塔[3]为主;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大致为中王国时期(第7~16王朝,含首尾两个混乱时期),建筑以石窟陵墓为主;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为新王国时期(第17~20王朝),建筑以阿蒙神庙与国王宫殿为主;此后古埃及一蹶不振,相继沦为来自西亚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属国,至公元前年,又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占领,由此开始了希腊化的时代。 我们从上可见古埃及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比较单调,在其漫长的帝国岁月里,虽然也经历过短暂的内部动乱和外族入侵,但总的来说政治状况相当稳定。这通常有利于建筑艺术的繁荣。同样是从上可见,陵墓建筑可谓古埃及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一个部类,而作为古王国时期法老陵墓的金字塔更堪称古埃及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物,这似乎颇能印证希腊史家卡洛斯对古埃及国民性的评价:“埃及人把住宅仅仅看作是旅舍,而把坟墓视为永久性的住宅”,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古埃及人是如此轻生厌世么?其实恰恰相反。 和别人一样,古埃及人非常惧怕死亡,但亚当后裔的生命存在是一个有始必有终的过程,对此,有人会问“为什么”,但多数人会问“怎么办”。东亚古代许多帝王明显属于后者,他们致力于寻找或炼制“仙药”,以求“长生不老”;而同样属乎后者的古埃及人却志不在此,他们对于此身必死这个现实似乎很早便选择了面对与接受,但在此基础上寄望于“复活”。他们相信,遗体必须完好无缺才能使游离的灵魂“卡”复归,因此便用非常复杂的方法将尸身制作成不易腐烂的“木乃伊”,然后暂厝于一种特制的“保鲜建筑”中,静静地等待复活——事实证明,金字塔这种巨大的四方锥形“保鲜建筑”对于保护尸体的确十分有效——这种信念使古埃及人的生活变得非常奇怪:为了不死,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坟墓;为了活着,他们每天都在准备死。他们因惧怕死亡而重视死亡,因眷恋今生而浪费今生。于是,一座座金字塔承载着法老王的厚望被建筑起来,在北非的万里流沙中静默地矗立了将近五千年,成为这个梦想永生不灭的已逝文明的绝妙象征。 公元前3世纪,著名闲人昂蒂帕克列举了当时的世界七大奇观[4],两千多年下来,随着时光流逝,有的被毁了,有的坍塌了,如今只剩下位居榜首的胡夫金字塔硕果仅存。无怪乎埃及有句谚语说:“人类畏惧时间,而时间畏惧金字塔。” 金字塔是如何做到的呢? 请做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定量的细砂、米粒和面粉,分别从上往下慢慢地倾倒,不久就会形成三个圆锥体,尽管它们质量不同,但形状却异常相似。假如你愿意测量一下,便会发现三者的锥角皆为52°。这种自然塌落形成的52°锥角是所有角中之最稳定者,被称为“自然塌落现象的极限角和稳定角”,而金字塔的锥角恰是51°50′9″。如此一来,当无坚不摧的沙漠风暴遭遇金字塔的时候,由于后者独特的“稳定角”造型,不得不沿着塔的斜面或棱角缓缓上升,使得塔的受风面由下而上愈来愈小,在到达塔顶时已趋近于零。这种巧妙化解破坏力的独特造型,正是金字塔在狂风肆虐的北非大漠中千年不倒的奥妙所在。 问题是,在年前,刚刚揖别史前蛮荒时代不久的古埃及人又是如何知道52°角是稳定角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不过话说回来,金字塔留给我们的谜团又岂止这一个?且不说它那能令尸体迅速脱水、食物保持新鲜、刀片延长寿命的奇异形体,也不说它那能与若干天文地理数据相吻合的神秘尺度,单说说它的建造吧——吉萨金字塔每块巨石重达2.5吨,要把它们提升到将近米的高度,即使对拥有起重设备的现代人来说都颇有难度,而年前连铁器都还尚未掌握的古埃及人是如何做到的?另据专家估算,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埃及帝国要营建金字塔这种骇人巨物必须拥有至少万居民,否则根本难以保障工程所需的劳动力和给养,但问题是直到公元前年,全世界的人口还不到万……金字塔身上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因此一直有人宣称它并非人类文明的产物,而是由所谓“外星人”建造的。 但实际上,考古人员已在金字塔附近地区发现了大量服役劳工的墓地及集体宿舍等生活设施的遗迹,并在死者随葬品中发现了不少用于测量、计算和加工石器的工具……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字塔确确实实是古代人类的杰作,准确地说,它们中的每一座都是古王国时期在专制帝国控制下的埃及劳工的集体劳动成果。既是人工产物,那也就意味着,金字塔这种近乎完美的建筑形制一定不会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演化、渐臻成熟的定型过程。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 起初,美尼斯国王所完成的政治大一统并没有影响到上下埃及百姓各自的生活方式,他们仍然遵循着各自的传统,发展着不同的文化,这在其陵墓建筑上反映得十分充分。上埃及人继承着其祖先将死者葬在远离居住区的沙地并在其上堆起一个沙丘的做法。而下埃及人则仍恪守着将死者直接埋在其住所地下的传统。直到后来,国王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通过行政手段干涉,才将两种不同的墓葬习俗强制性归一,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模式化的“马斯塔巴”建筑,即由砖砌造的一种长方形平台式陵墓,从此成为定式。马斯塔巴的建筑造型与当时的贵族府邸如出一辙,显然,当时的人们只能根据日常生活的情形来设想死后的光景,工匠们也只能以其最熟悉的建筑物(居室)为蓝本来设计其他种类建筑的造型。单纯、素朴的思维造就单纯、素朴的建筑。 到古王国时期(始于第3王朝),埃及的中央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第3王朝的开国法老昭赛尔(Zoser)集宗教、政治、经济与军事大权于一身,踌躇满志、自命为太阳神拉(Re)之子的他无法接受自己百年之后仍被葬于一个普通的马斯塔巴中,他希望自己的陵墓能成为一个供千秋万代瞻仰的纪念性建筑物。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想法被宰相伊姆霍特普(Imhotep)知道了。 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伊姆霍特普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昭赛尔实现梦想,无论它是多么疯狂。国王既然不想安息在一个普通的砖砌马斯塔巴中,伊姆霍特普便突破成规,为主人营建了一座规模空前的石造马斯塔巴,但这并不能使昭赛尔王满意。 伊姆霍特普幡然醒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材料和体量,而在于创意。于是别出心裁,在已建成的巨型马斯塔巴上面又加建了5个一层比一层小的马斯塔巴,由此形成的6级踏步恰好隐喻“法老亡灵升天的阶梯”。这座构思巧妙、造型如山的台阶式陵墓便是世界上的第一座金字塔——昭赛尔金字塔,它不仅获得了极难伺候的昭赛尔王的首肯,而且为设计者伊姆霍特普赢得了“史上首位官方建筑师”的美名。 这座位于萨卡拉的“始祖金字塔”高61.2米,建在长方形的地基上,基底南北长.4米,东西长.3米,尚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正方锥体的形制。 昭塞尔和伊姆霍特普,这对君臣开启了埃及历史的金字塔时代。在他们之后,古王国的历代君王竞相效仿,纷纷为自己建造更高、更大的金字塔陵墓。该种建筑形制也就不断向前探索、发展,终于在第4王朝时达到了自己的成熟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吉萨三塔”。它们坐落于开罗附近的吉萨,是古王国第4王朝时期的胡夫(Khufu)、哈夫拉(Khafra)、门考拉(Menkaura)三代法老的陵墓。 其中胡夫金字塔最高,.59米,相当于我们今日50层楼房的高度,直至年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建成,胡夫王的陵墓在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占据着人类建筑的制高点。塔基四边各长米,正对着东南西北四方,误差少于1°。整幢陵墓大约由万块巨石砌成,平均每块重达2.5吨,相当于一辆小汽车,而个别大块头者甚至超过15吨。不同于多年前的昭赛尔金字塔的“六步台阶式”,胡夫金字塔是斜面无阶的真正的方锥体建筑,这不仅反映了建筑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意味着建筑寓意的变迁:如果说台阶式金字塔的踏步造型表达了法老对于亡魂升天的憧憬,那么无阶式金字塔的斜面形制则明显是在炫耀法老作为太阳神之子的光华四射的神威[5]。这是君权得到进一步强化乃至神化的一种表现。 哈夫拉金字塔较胡夫金字塔略小一点点,高.5米,塔基四边长.5米。该塔祭堂的门厅旁边,屹立着举世闻名的大斯芬克斯(即狮身人面像)[6],它的写实性和金字塔的抽象性相对比,使整个建筑群富有变化,更形完美。 三塔中规模最小的门考拉金字塔亦相当于今日一座20多层的摩天楼,有66.5米高,底边各长.5米。 吉萨三塔都是正方位的,但互以对角线相接,造成建筑群参差错落的轮廓。若论具体布局,三塔的排列则被认为与猎户座中三粒腰星的排列有着特殊关系。猎户座是古埃及人心目中的众神居所、天堂所在。据说,利用电脑模拟回到公元前年,天上跨越子午线的猎户三星的格局与地上吉萨三塔的排列若合符节,而天上星河与地上尼罗河的位置分布也全然对称。这种天地相应的关系若然存在,当非全然巧合,古埃及人的朴素信仰和华丽手段令人有此信心。但需要提防的是坊间某些畅销书作者,为了畅销他们可以“推论”出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同样也可以“有理有据”地告诉你金字塔的设计师居住在猎户座星云。 除了金字塔,古埃及最著名的建筑物当属阿蒙神庙。刚刚说过,古埃及人的信仰较其科技要简陋得多,属于古代世界并不鲜见的多神宗教,他们所崇奉的很多“神明”是动物,如眼镜蛇、鹰、猫等。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这种图腾崇拜的形成似乎也无甚难解之处,走出乐园的人类在大地上属于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他们捕食不如虎狼凶猛,奔跑也不如羚羊神速,与很多动物相比,他们的存在都显得那么柔弱卑微,因此便如蒋勋所说,流传于人间后世的许多神话故事都保留了当时人类不愿当人的记录。人不愿意做人,于是便开始幻想自己的祖先不是人。蒋氏文章,不足采信者多,然此说不在斯列。对于自身价值懵然无知的失乐园者,开始盼望自己拥有凶禽猛兽的蛮力,渐渐地,也就把它们附会成自己的神圣祖先。埃及荷鲁斯的鹰首人身、希腊大斯芬克斯的狮身人面、华夏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例证实在多得很。除了这种拟人化了的动物,多神教所崇拜的神灵,还有很多是人格化了的自然体或自然力,如高山、大漠、长河、空气等,埃及的众多神祇中地位最高的太阳神亦属此类。位高香火旺,太阳神既为仙班领袖,所以太阳神庙也就遍布埃及各地。关于宗教信仰,古埃及人还有一个可笑处,即惯于将各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的守护神附会为太阳神的化身,因此太阳神的具体所指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变动,鹰神“荷鲁斯”、伊乌努的守护神“拉”都曾担任过太阳神,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年)埃及首都迁至底比斯后,底比斯的地方神“阿蒙”便开始凌驾于其他诸神之上,从此太阳神庙便称“阿蒙神庙”。 古埃及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经济主体的大一统帝国,君权之重堪比大清,不宁唯是,法老还是所谓“太阳神之子”,将神权与政权集于一身,具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到后来甚至发展到法老宣称与太阳神相结合、成为“在世天神”。当官员朝见法老时,必须下跪而且匍匐在他脚下,并以吻他脚前的尘土为荣。就这样,随着君王的神化,本来用于祀奉太阳神的阿蒙神庙也逐渐演变成为崇拜法老本人的纪念堂了。于是,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神庙建筑几乎遍布埃及每一片土地,用地面积在一个时期内居然占到了整个埃及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 古埃及最大的阿蒙神庙是开罗以南千米处、尼罗河东岸的卡纳克阿蒙神庙。卡纳克神庙是埃及中王国及新王国时期的首都底比斯的一部分,太阳神阿蒙的崇拜中心,古埃及最大的宗教场所。它的建造时间很长,大约始建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的中王国时期,一直扩建到公元前后希腊人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前后共营建了年之久,最终形成一片约25万平方米的巨大的综合建筑群,整体规模为世界宗教建筑之最。 建筑群的核心是阿蒙·拉大神庙,它占地多平方米,雄伟壮丽,是名副其实的古代建筑瑰宝,该庙宇尤以主神殿内密密麻麻排列着的根粗壮大石柱最令人称道,其中中央通道两旁的12根带有伞形纸草花柱头的大柱,高达23米,每根柱子的直径约3.5米,为世界之最。杰克·特里希德说,“在古代世界,柱子的象征意义极为重要,它代表着神明的力量和权威,也代表着生命力”,巨石柱作为古埃及神庙建筑的代表性构件,似乎恰好印证此说。 阿蒙神庙入口的式样也颇具特色。通常皆以两堵高大的梯形石墙夹着一线窄窄的入口门道-——与东亚的汉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看上去仿佛是整堵高墙中间被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两旁对称布置着一两组法老王的圆雕坐像,雕像之前又竖有一两组方尖碑。碑体造型为方形,向上逐渐收分,至顶端则与金字塔如出一辙,成为方锥体,寓意也与金字塔相同,体现着对于光华万丈的太阳神的崇拜。古埃及方尖碑最高可达30多米,比例通常为10:1,其瘦削的剪影恰可反衬背景石墙的高大厚重,二者间的强烈对比使得各自的特点益发鲜明,丰富了神庙入口的立面构图。 按弗洛伊德学派的说法,方尖碑(以及所有笔直或纵向的建筑物)都象征着性的意涵,即所谓阳具崇拜。此说对于方尖碑的设计初衷,即便言中,也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多神教中生殖崇拜的又一道具而已,性质与奥地利出土的“维伦多夫的维纳斯”无异,同属“堕落后的光景,而非原始的光景”,这在多神教社会里实属司空见惯,无须拍案惊奇。 在方尖碑之外,一条长达2公里的“狮身羊面像神道”将卡纳克神庙与南部的另一神庙——卢克索连接起来,后者也同样用于供奉太阳神。尼罗河亦将这两座神城以水路相连,在某些庆典节期,太阳神阿蒙的雕像会被披红挂绿装载上船,在一列小船的护送下,从卡纳克运至卢克索“巡游”。 在古埃及,与埋葬死人的陵墓和崇拜神明的庙宇相比,活人的建筑原是微不足道的,但对“太阳神之子”-——法老的房子则要另当别论。古埃及的王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法老的神性基础上,君权神化的程度非但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减弱,反倒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制集权制度的强化而与日俱增。发展到新王国时期,法老已不仅仅是“太阳神之子”的身份,而开始升级为“众神之神”、“宇宙秩序之中心”了。至此,奢华的宫殿显然不再能配得上其至上的尊荣,于是便只好为其兴建神庙,以祭神的方式来事君。如卡宏城的法老王宫就已经和阿蒙神庙结为一体,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新王国晚期的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II,前年—前7年在位)在尼罗河上游为自己营建的岩凿建筑-——拉布·辛博神庙。 拉美西斯二世是古埃及第19王朝的第3任法老王,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凭着如日中天的国力,拉美西斯二世在埃及的国土上大兴土木,留下无数殿堂庙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座开凿于公元前年左右的岩凿神庙。该建筑集太阳神庙和拉美西斯纪念堂于一身,其内部空间被分隔成三个段落,分别为前室、多柱大厅和圣堂,这可以说是开了后世西方“三段式”建筑空间之先河。不同于古代东亚大陆“三段式”建筑空间的横向排列,左、中、右连接,人自长边进入室内的特点;拉布·辛博神庙的三段空间是纵向排列,前、中、后连接,人自短边进入。因此,参观该庙便成为一个在长达60米的进深轴上不断向前深入的过程,愈深入离人间就愈远,空间神秘感就愈强,对神明(或法老)之伟大与自身之渺小的体认就愈深刻,情绪一路上被空间如此“压迫折磨”,等走到尽端的圣堂(象征着神明的领域)时,已是意气消融,内心深处的膜拜的本能被环境油然唤醒,“五体投地”便成为必然反应。而这正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拉布·辛博神庙的这种纵向布局、短边进入的狭长式空间格局对后世西方的神庙、教堂建筑的影响极大。 在每年的2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生日,以及10月21日拉美西斯二世加冕日这两天,阳光可以奇迹般地透射过60米深的狭长庙廊,精准地洒在被供奉于神庙尽端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上[7],而他周围的雕像便享受不到太阳神这份奇妙的恩典。对于研究人类建筑史的人来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不知道,但对“神明”的“制造过程”却须心如明镜。在这个“行当”中,法老御用的埃及大工匠们绝对堪称高手。当然,这对被神化者(其实也就是主其事者)的心理素质也有相当的要求,恰好拉美西斯二世又是一位心理素质极佳的君王,可以坦然设计并接受这一切。于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位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法老在位期间,几乎将自己的神庙和塑像建遍了埃及的每一片土地,其兴建之频,数量之多,密度之大,世上无出其右者。别的不提,就说这拉布·辛博神庙门洞前的那四尊高耸入云(约20多米)的巨石神像吧,竟也都是他自己的形象!由此可见,希伯来奴隶选择在他当政期间集体出走(约在公元前年)绝非凑巧[8]。(插图02-1) 关于希伯来奴隶出埃及的故事,可谓说来话长。 我们先说一件并非不相干的往事。前面说过,埃及历史整体而言相当单纯,这与其地理格局的封闭有关,也与尼罗河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关,自从美尼斯一统埃及,古埃及人过了多年遗世而独立的生活。不料在中王国的晚期(公元前17世纪),一个号称“喜克索斯人(Hyksos)”的阿拉伯野蛮部落闯入了埃及的历史舞台,这些来自亚洲的征服者从埃及东北部侵入尼罗河流域,占领北方并定都阿瓦利斯(Avaris),建立起古埃及史上的第15王朝,对尼罗河谷进行了长达多年的异族统治。前朝衣冠被迫南渡,偏安于以底比斯为中心的南方一隅,凄凄惶惶一如12世纪亚洲的南宋王朝。 尼罗河畔的埃及帝国,在古代世界堪称“温柔富贵之乡”,广土众民,文明昌盛,因此吸引了很多其他民族的人来此地求生存谋发展,尤其是与其接壤的西亚地区的那些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断寻找新牧场的游牧民族。这其中就有一户牧人家族,他们的祖籍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幼发拉底河河口的吾珥城(Ur,今伊拉克境内),被人们称为“希伯来人”。 这支希伯来牧羊人部落,大约在公元前年因饥荒而迁入了富庶的埃及,在歌珊地区定居下来。在古老的《创世记》中,这个故事是这样记载的: 虽然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但人类历史并没有因此戛然而止,因为上帝有一个惊人的救赎计划。为此,上帝拣选了一个家族。约在公元前19-18世纪,上帝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他对上帝的话深信不疑,坚决奉行,被后世称为“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原籍在迦勒底的吾珥,那是一个充满偶像崇拜的繁华都市,所以上帝带领他离开本土,经哈兰,前往迦南地(今巴勒斯坦一带),并立约应许将这片“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为产业,还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年近百岁的亚伯拉罕对此深信不疑,虽然这时他还没有子嗣。 迦南地的居民称亚伯拉罕一家为“东边来的越河者”,“越河者”的迦南语读音为“希伯来”(Iberi相当英语Hebrew)。 后来亚伯拉罕生下了以实玛利和以撒,庶出的以实玛利即后来阿拉伯人的祖先,上帝拣选了嫡出的以撒。 以撒生下了以扫和雅各,上帝拣选了雅各。雅各又名以色列(意为“神的王子”),所以雅各的后人也被称为以色列人。 上帝向以撒和以色列父子重申了其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色列晚年全家六十多口因饥荒从迦南逃到埃及,在埃及寄居了年,成为一支万人口的大族,这便是以色列民族。 如前所述,公元前17世纪的埃及正处于喜克索斯人的异族统治之下,以色列一家此时迁来埃及,其情形一如马可·波罗(MarcoPolo)13世纪时来到华夏世界,所见到的并非这个文明圈的寻常面貌。不过这恐怕也正是他们的幸运之处,征服者通常较本土君王更能善待远方的宾客,马可·波罗与大元皇帝忽必烈的友谊便是一例,更何况喜克索斯人和以色列一家基本同属亚洲的闪族人种,亚伯拉罕的后裔迁入埃及可谓正逢其时。 公元前年左右,在底比斯偏安已久的埃及人开始北伐,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阿赫摩斯一世的领导下,推翻了喜克索斯人的异族统治,将“鞑虏”们悉数逐出了尼罗河谷,重光埃及,开启了历史上的新王国时期(公元前—公元前)。 埃及的光复对以色列人来说恐怕并非什么好消息,因为他们和喜克索斯人属同一种族,曾在喜克索斯人的治下被善待过,他们的一位先祖约瑟(以色列第十一子)甚至担当过希克索斯王朝的首相。如今,在前朝的所有功劳和优裕都成了一种罪过,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引自《出埃及记》) 果然,从此以色列人就大祸临头了。他们被贬为最卑贱的奴隶,被迫由埃及士兵看守着服各种苦役:开荒种地,和泥制砖,并充当廉价劳动力为法老修建仓城、神庙和宫殿等大型建筑,生活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以色列人却仍然繁衍不绝,人丁兴旺,这更引起了埃及法老塞提一世的恐慌和嫉恨,于是下令溺死所有以色列人的新生男婴。这在当时是灭绝一个民族的最好办法。 这时有一对以色列夫妇,他们不合时宜地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母亲爱子心切,不忍溺杀,就将儿子悄悄地藏了起来。过了三个月,实在藏不住了,她把儿子抱到了尼罗河边,盛在一个涂了石漆与石油的纸草(一作“蒲草”)箱子里,推入了尼罗河的芦荻丛中。 恰巧埃及的公主下河洗澡,发现芦荻丛中漂来一只箱子,就唤宫女去取来。打开一看竟是个俊美的婴儿,还呱呱啼叫,遂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收他为养子,取名摩西(希伯来文与“捞起”谐音),以纪念这是一个从水中捞出来的孩子。这个孩子的传奇的一生就此拉开了帷幕,一个民族也从此改变了命运。(插图02-2) 此时的公主或许尚待字闺中,对育儿常识一无所知,便命宫女去请个保姆来。 摩西有个姐姐,名叫米莲,一直躲在不远处窥视。这时就走上前来对公主说,她们村庄有个以色列妇人正适合照顾这么大的婴儿。 她飞跑回家带来了自己的母亲。 这样,以色列男孩摩西便逃脱了大屠杀,且在亲生母亲隐姓埋名的精心呵护下成长了起来,并受到了埃及王公贵族式的良好教育。 这是古代史诗中屡见不鲜的“杀婴/漂水/领养”的母体模式,明代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中亦有类似情节,而在《出埃及记》中的描写却别具深意:原来,摩西母亲所用的“箱子”,跟《创世记》中挪亚避洪水的“方舟”在希伯来文中是同一词汇,皆象征着上帝的“救赎之手”。而用来编制这“箱子”的纸草,在建筑史上很值得一提。由于尼罗河流域缺少良好木材,古埃及的史前建筑及后来普通民众的简陋房舍,都是以这种东西为基本材料,结合棕榈木、芦苇与土坯等一起搭建起来的;另外,根据文本情境,我们也不难判断,石漆与石油作为防水材料,在彼时埃及社会当属人尽皆知的常识了。 转眼摩西长大成人,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次为解救一个以色列苦力而怒杀埃及监工,走漏风声后逃亡至米甸,路遇几名受到欺负的牧羊女,便挺身而出搭救了她们——此时他并不知道她们是米甸祭司叶特罗的千金小姐。祭司喜欢摩西,遂将一女许配与他,招其为婿。一日,摩西赶着岳父的羊群来到荒野里的西奈山放牧,忽见一丛荆棘起火,烈焰中有声音呼唤他。原来是上帝为拯救在异邦为奴的以色列民,拣选摩西做了先知,命他返回埃及带领同胞们挣脱法老的奴役。摩西历经千辛万苦,费尽周折,终于在公元前年前后[9],率领以色列人成功地逃脱了其童年时的玩伴——拉美西斯二世的军队的追击,出埃及,越红海,前往上帝应许给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片“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布伦达·查普曼导演的一部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所讲述的就是这个古老故事。 在途经西奈旷野时,上帝藉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拣选他们为其特殊“选民”,并为他们制定了以“十诫”为核心的全备的律例和典章制度。十诫的第一条是“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上帝,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奠定了人类一神教的信仰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大;第二条是“不可雕刻、膜拜偶像”,则明确反对视觉主义的倾向,上帝远非视觉所能及,他要人听他的话而非追求眼睛明亮,这奠定了以色列民族及受其影响的其他民族“重语言,轻形象”的文化传统,使他们日后各种艺术作品(包括建筑)的风格迥异于其他所有民族;此外,还有“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要守安息日”、“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伪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财产”。这些诫命不仅奠定了人类道德的基础,而且更重要的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中最早的犹太教也由此正式形成,后来对人类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与它紧密相关。 犹太教历史上的第一座“宗教建筑”,当属摩西在出埃及途中主持建造的圣幕,也叫会幕,它是一个流动的敬拜耶和华的中心场所,也是我们无论研究建筑史还是宗教史的时候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因为若忽略了它,我们将无法理解后来(公元前10世纪)所罗门王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的空间含义。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时虽曾参与建造过许多神庙、王宫,但他们在西奈旷野中营建的圣幕却丝毫没有受到埃及建筑形制的影响。据《出埃及记》,摩西圣幕乃是出于神启:“耶和华晓谕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10]”希伯来语圣经中详细记载了圣幕的空间格局及其室内陈设的具体材料、尺寸、颜色以及细部构造。整体观之我们会发现,这圣幕真是与埃及建筑学毫不相干,反而跟后来东亚帝都“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相套”的空间模式有几分相似,至圣所与圣所、外院两重相套:外围的院子系用帷子在旷野中遮拦而成;院子当中用帐幕围合出圣所来,这是用来放置陈设饼桌子、金灯台与香坛的地方;圣所的尽端是一道隔断的幔子,幔子后即为至圣所,专门放置耶和华的施恩座与约柜[11],表示上帝的临在。 在整座圣幕中,那幅以巧匠的手工绣着基路伯天使的幔子特别值得白癜风怎样治疗好得快北京中科医院十二年专注白癜风医学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ls/3478.html
- 上一篇文章: 成功转学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我都做了哪些
- 下一篇文章: 艺界广州65层的摩天景观精英艺术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