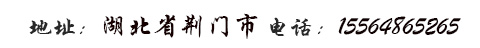孙俊武友德丨秦汉西南汉夷格局以
|
摘要:通过《华阳国志》与考古发现墓葬分布状况的对比分析,初步得出汉末西南地区的“汉夷”格局大体上是: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巴西郡、梓潼郡、汉中郡,并巴郡、巴东郡的长江沿线、汉嘉郡东北部至东汉时已有大量汉族的分布;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虽无大姓、士女的记载,然为秦汉汉族移民重要区域,当以汉族为主;宕渠郡、巴郡和巴东郡的长江以北,并朱提郡、平夷郡、平乐郡、建宁郡、晋宁郡、夜郎郡地区,有较少数量的大姓、士女,这些区域不仅有大量“夷”的分布且体现为汉族聚居地区“汉夷共处”的格局;《华阳国志》余下区域,多只有局部且数量不多的大姓、士女、室墓、崖墓的分布,当是以“夷”为主的区域。 关键词:中国西南秦汉汉夷格局《华阳国志》 于秦汉的西南地区而言,《史记》、《汉书》、《后汉书》列有“西南夷”传,始有系统的史志材料;晋人常璩撰《华阳国志》,为西南地区最早的区域性史志材料,论述更为详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华阳国志》各志除叙述一般的历史外,对各区的豪族大姓、士女、“蛮夷”有特别的说明,本文以其为秦汉西南地区“汉夷”格局的窗口,并结合考古文化中的石、砖室墓和崖墓及其数量的分布对秦汉西南的“汉夷”格局作一分析。 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以《华阳国志》政区作为分析秦汉西南地区“汉夷”格局的基本政治单元,其范围包含今云南、贵州、重庆全境,四川中、东部,甘肃东南角,陕西西南角,湖北西南、西北角。在时间上,《华阳国志》所载豪族大姓包括汉晋时期,士女则分西汉、东汉、蜀汉、晋四期。因晋时士女数较少,本文未统计,西汉、东汉、蜀汉士女则分期标示。室墓的分布分西汉、东汉两期,崖墓则均属于东汉时期。 一、《华阳国志》豪族士女分布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华阳国志》的豪族大姓主要在前四卷各郡县志述及,并同时对各郡县“蛮夷”有交待,但在分期上较为模糊。士女的分布是专列《序志并士女目录》给出的,且有分期,是以士女及其数量的分布不仅能够看出汉末的“汉夷”格局来,而且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西汉、东汉、蜀汉时期的“汉夷”格局演进。豪族大姓及其数量与“蛮夷”分布,士女及其数量的分布,并见表1、表2。 ?表1.《华阳国志》诸郡大姓与“蛮夷”分布表 郡名 大姓与“蛮夷”分布记载 巴郡 江州县(治所在今重庆市北,辖今巴、江北、江津、綦、南川、壁山、永川诸县)冠族有波、鈆、毋、谢、然、瓂、杨、白、上官、程、常(刘表缺“常”,多“愠”);枳县有章、常、连、黎、牟、阳诸冠族;临江县,有严、甘、文、杨、杜诸大姓;平都县,有殷、吕、蔡氏;垫江县,黎、夏、杜为大姓。 巴东郡 郡有奴、獽、夷、蜑诸蛮民。朐忍县有扶、先、徐大姓。南浦县“主夷”。 涪陵郡 郡多獽、蜑之民,又有蟾夷。郡有豪族徐、蔺、谢、范,大姓有韩、蒋(刘表未列,然《华阳国志》云韩、蒋二氏“世掌交部曲,为大姓”,故列)。 巴西郡 阆中县有三狐、五马、蒲、赵、任、黄、严诸大姓;南充国县,大姓有侯、谯;安汉县,大姓有陈、范、阎、赵。 宕渠郡 汉昌县有大姓勾氏。 汉中郡 南郑县有李、程、赵大姓。 魏兴郡 本汉中西城县,无大姓记载。 此三郡,常璩自己说“未能详其小委曲也”,但多处提及为汉罪人流徙之地,有汉人无疑。 上庸郡 无大姓记载。 新城郡 无大姓记载。 梓潼郡 本广汉属县。梓潼县有文、景、雍、邓四大姓;涪县,大姓杨、杜、李;晋寿县,《华阳国志》云“大姓葬此者多”,可知有一定数量的大姓存在。 武都郡 以氐傁、羌、戎为主。 阴平郡 多氐傁,有黑水羌、白水羌、紫羌。 蜀郡 成都县有大姓柳、杜、张、赵、郭、杨,并有豪富程郑、郄公、郭子平,奢豪杨伯侯兄弟(刘表缺后两类姓;此两类部分姓与前姓同,但常璩列为不同两类大姓,并采);郫县有大姓何、罗、郭;繁县,三张为甲族;江原县,东方常氏为大姓(刘表为“东方、常氏”,可采);临邛县,陈、刘二氏为大姓;广都县,朱氏为首族,有獽、蜑之民。 广汉郡 郡有羌反之事。雒县豪族有镡、李、郭、翟;绵竹县,首族为秦、杜;什坊县,杨氏为大姓;新都县,杨厚、董扶为名士,又有马、史、汝、郑四姓,计六姓(刘表缺前两姓,然名士所出当在大姓家族,常璩“又有”或已表此意,列);郪县,大姓王、李氏,又有巴、高家;广汉县,彭、段为甲族;德阳县,“康、古、袁氏四姓”(刘表亦为“四姓”,疑有脱字)。 犍为郡 武阳县多大姓,七杨、五李,共十二姓;南安县有能、宣、谢、审四姓,杨、费等五大族(刘表亦“四大姓”、“五大族”并举,常氏此当有省文);僰道县,有大姓吴、隗、楚、石、薛、相;牛鞭县,程、韩为冠族;资中县,王、董、张、赵为望族。 江阳郡 江阳县有大姓王、孙、程、郑,八族赵、魏、先、周等;汉安县有大姓程、姚、郭、石,八族张、季、李、赵等;新乐县有大姓魏、吕二氏。 汶山郡 有六夷、羌虏、羌胡、白兰峒等九种之戎,牛马、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羖之属。 汉嘉郡 缺。 越巂郡 郡有越巂叟。邛都原有七部,后为七中营兵;苏示县,有夷;定笮县,多夷。 牂柯郡 郡有大姓龙、傅、尹、董,有平夷之记载,郡治县为万寿县。《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大姓龙、傅、尹、董在句町县,据此。然《华阳国志》此四姓当在兴古郡而非牂柯郡。 平夷郡 鄨县有大姓王氏。 夜郎郡 无大姓之记。 晋宁郡 无大姓之记。 建宁郡 郡有五部都尉、四姓及霍家部曲,后二者当为豪族大姓,共五姓。同乐县有大姓爨氏。谈稿县濮、獠居之,伶丘县“主獠”。 平乐郡 不详。 朱提郡 郡有大姓朱、鲁、雷、兴、伊、递、高、李。 南广郡 无大姓之记。 永昌郡 郡有穿胸、儋耳种,鸠僚、“诸”濮等族群。不韦县豪族吕氏,并四大姓陈、赵、谢、杨为五姓(刘表仅列陈、赵、杨三姓)。 云南郡 不详。 河阳郡 缺。 梁水郡 不详。 兴古郡 多鸠僚、濮。龙、傅、尹、董在句町县(参前牂柯郡注)。 西平郡 多夷。 资料来源:据《华阳国志》整理。笔者整理完该表后,得见刘增贵先生《汉代的益州士族》(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一文已有该表,然与本表略有差异,表文已括注。 ?表2.《华阳国志》士女籍贯可考者统计表 郡 县 士 列女 郡 县 士 列女 西汉 东汉 蜀汉 西汉 东汉 蜀汉 蜀郡 成都 7 22 4 2 广汉郡(续) 郪 13 5 1 临邛 3 1 1 德阳 2 郫 3 3 3 3 犍为郡 武阳 13 3 2 江原 2 5 1 3 资中 5 1 (新)繁 2 2 1 南安 4 2 2 严道 1 僰道 4 3 广都 1 1 牛鞞 1 巴郡 江州 3 汉中郡 成固 4 6 3 临江 1 褒中 1 垫江 4 南郑 19 6 巴西郡 阆中 11 6 11 4 梓潼郡 梓潼 8 1 1 安汉 8 2 2 涪 4 5 2 南充国 1 汉嘉郡 2 西充国 2 牂柯郡 毋敛 1 宕渠郡 宕渠 1 10 1 2 平夷 1 汉昌 1 魏兴郡 西城 1 广汉郡 新都 10 1 1 永昌郡 不韦 1 绵竹 7 2 2 建宁郡 3 雒 13 1 朱提郡 1 什坊 2 江阳郡 江阳 1 广汉 7 1 3 符 2 表2中,士女存在较多父子、父女、兄弟、兄妹关系情况,往往只有父、兄籍贯明确,故子、女、弟、妹皆从父、从兄。另有特殊者并各郡情况如下: 蜀郡,共79人。其中,1人生平失载,4人属县不详,共5人不详。此外,列女张叔纪,本注“霸女孙也”。《华阳国志》载有郫人何霸,成都人张霸,张叔纪当原籍成都。邓通,《华阳国志》所载籍贯不详,只知在蜀郡。《史记》卷《佞幸列传》邓通条云邓通为南安县人,在《华阳国志》政区中当在犍为郡,统计时计入犍为郡南安县。王褒,资中人,资中在《华阳国志》中当为犍为郡。巴郡,亦79人。8人不详,1人失载,共9人不详。赵英为赵璝之女,赵璝阆中人。广汉郡,共72人。列女失载1人。犍为郡,共41人。原注本“三十八人”,但另有三人当在犍为郡:贾龙,因其事不详常氏未计入该郡士女数中,但计总人数时可计入;邓通、王褒,均参见蜀郡注。汉中郡,共49人。其中有10人记载不详。此外,列女李穆姜为李法之妹,李法南郑人,李穆姜籍贯从兄。刘泰瑛,刘巨公女,从父,刘巨公为南郑人。李文姬,本注“太尉固女”,“太尉固”当即李固。李固父李郃,李郃父李颉,均为南郑人。陈顺谦,本注“陈伯台从女也”。陈伯台即巴郡太守陈雅,字伯台,成固人。陈惠谦,顺谦妹,从父,成固人。梓潼郡,共21人。汉嘉郡,共2人。牂柯郡,2人。原注3人,但其中的谢恕当为晋人,刘琳已注,故本表实只录汉时郡2人。魏兴郡,1人。永昌郡,1人。原本无士女,但吕凯事在建兴年,可列入蜀汉。建宁郡,3人,属县均不详。其中,李恢列入蜀汉;爂习为李恢姑父,大致生活在东汉末;孟获生活在东汉末至蜀汉时期,本南夷。朱提郡1人。江阳郡3人。 从上表中能够观察到,两汉西南地区士人的发展除了时间上的巨大变化外,空间上亦有较大的变化:西汉时,西南士人仅集中于蜀郡、巴郡;东汉时,士人较多的郡县扩展至广汉郡、犍为郡;牂牁郡、永昌郡终两汉士人分布较少。这些士人的分布,一般来说与汉移民有直接的关系。 大姓的问题相比士女来说要复杂一些。许倬云曾认为:“大姓之所在,当可作为汉人移民所至的指标。”此说大体正确,但大姓的来源并非只包括汉族群体。任乃强已注意到,巴郡江州的波、鈆、毋、谢、然等十一姓多是中原所无之稀姓,当是土著群体。此外,牂牁地区毋敛人尹珍因学习汉文化并在南中兴学被列入大姓,傅宝因随太守镇压反叛而被列入大姓,亦可见部分大姓是来源于“西南夷”的。考古文化上,成都站东乡汉墓群3号墓中“宴饮图”和“传经图”中的人物,全是“左衽”,按《史记》、《汉书》、《后汉书》“西南夷”部分群体“披发左衽”的说法这些人物当是“夷”无疑,然解为“宴饮图”和“传经图”即表明墓主已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了,这类人物当即《华阳国志》中汉化了的大姓。当然,并非所有对西南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的土著群体都会被《华阳国志》列为大姓,如武都郡的李雄、刘曜、石勒、石虎、张骏,阴平郡的毛深、左腾,南中地区的部曲焦、雍、量、爨、孟、毛、娄、李诸氏,多不在《华阳国志》大姓之列,其中南中的孟氏考古资料证明当时任职颇高。事实上,《华阳国志》所载大姓多见于《益部耆旧传》。而在《益部耆旧传》中,大姓来源情况有四:其一,见载最多的是入蜀为官或者讲学的士人,虽未言明族系,但大体上可视为汉族。其二,出蜀为官的士人,其数量也比较多,说明在两汉时期蜀地汉文化与中原地区趋同,并且在政治上有较重要的影响。其三,徙入蜀地的士人,如胡安,曾“聚徙”白鹤山,说明迁入该地时并不止胡安一人。胡安原为临邛人,当属“夷”系群体。其四,外地入蜀依靠“夷”人而获得政治地位者,如张宽,《益部耆旧传》载汉武帝时与蜀郡怪异女子婚配而为大姓,具有神话的成分,可理解为依靠当地人而获得政治地位。 总之《华阳国志》所载大姓、士女,有汉移民,亦有相当比例的汉化夷人。可以将大姓、士女的分布作为汉族移民和分布的一个“指标”,但也要考虑族群融合的因素。此外,形成大姓并有士女见载当有一定的条件,大姓、士女只是秦汉西南地区汉族的“精英分子”,汉族的分布格局及其所带来的“汉夷”格局当结合其他史料分析之,下节即本此而论,最后再以考古材料比较之。 二、豪族大姓、士女的空间结构与秦汉汉族移民格局 前节表列《华阳国志》中的大姓、士女目录在该书中的角色并不是旁白性的,也不仅仅是列举诸贤而已。常璩在《华阳国志》卷12《序志》中说到了撰写的缘由:一者,秦汉诸传中涉及西南人物时时有偏颇;二者,书诸仁人志士的著作已见于《益部耆旧传》,但尤重成都地区;三者,秦、汉、晋三代郡县分置、地名变更频繁。换言之,常璩撰写《华阳国志》的材料来源和目的都与“华阳”的士人传记、政区沿革有直接的关系。从这点来看,统计《华阳国志》中的大姓、士女这一类汉人群体中的代表性人物来分析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汉族格局并不是近来研究者的创造,常璩在前四卷中对各郡士人概况是有所交待的。此外,常璩的叙述在详细记载士人结构的诸郡中存在一定的次序,比如“冠冕三巴”、“于西州为盛”、“殊于诸郡”等就表述表明了汉族群体不同特征在空间上的差异与次序。 汉族群体空间结构及其次序的形成需要一些条件。从时空条件上说,在空间层面上,需要有大量的汉民移入,否则零星的汉人移入则会被迅速“夷化”;在时间层面上,汉民移入要较早并有所发展,否则难以形成具有识别意义的汉文化区域,自然不会有豪族大姓、士女的说法。以史料观之,前节豪族大姓、士女及其数量的分布,并本节各郡士人结构空间特征,都能够证明这一点,现依主要区域的空间次序叙述如下。 汉中地区,在《华阳国志》中大姓记载不详,士女数量较多。而对士人的评价中,《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汉中郡条说该郡文教倡盛,名士众多,是汉代的宰相之乡,所出州牧郡守在西州中是最多的。这是所见对诸郡士人情况评价最高的。所谓“西州”,当源自汉代“西州”、“北州”、“东州””、“南州”、“中州”之说,“西州”初指益州,东汉主要指凉州、朔方地区,常璩所说“西州”则当包括益州。梓潼郡地处褒斜道至成都的交通干道,是秦汉时期汉族移民的主要通道,虽无史料记载有汉族群体移入该郡,但实有不少汉族群体居住。《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阴平郡条记载到:“汉安帝永初二年,羌反,烧郡城,郡人退住白水。”白水即白水关,只有梓潼郡有较多汉人分布的情况下才能有“郡人退住白水”一说。此外,该郡有不少大姓的分布,《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梓潼郡条更云该郡士人“侔于巴、蜀”,在常璩眼中是较重要的汉文化区域。 在汉族移民史料上,秦汉时期汉中移民的记载并不多。《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九年(前年),嫪毐作乱被杀,“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若按每家五人计算,约有二万人。两年后,嫪毐群体部分人口又被徙往成都。《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载始皇十一年,徙吕不韦“家属”入蜀,《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新城郡条则说“秦始皇徙吕不韦舍人万家于房陵”,则此次徙民之数至少达到五六万人。尽管汉中地区汉族移民史料有限,但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可大体确定两汉时期汉中地区已成为重要的汉文化区域。一方面,汉中地区长期以来属于华夷分野的区域,在商周时期有不少属华夏体系的方国存在。比如,上庸郡本即故庸国地,故庸国居民庸人本为周的筑城奴仆一类,在身份上本即属华夏体系,在汉时当演变为汉族群体。另一方面,汉中地区在两汉特别是西汉时期是宗族大姓迁徙比较集中的区域,《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新城郡条云房陵县曰:“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据葛剑雄所考,西汉时期被迁往汉中地区的王就有九人,其中房陵郡六王,上庸郡二王,汉中郡一王。王族迁徙一般都有一定规模的人口随迁,而这些人口又多士人。被迁至汉中地区的王就有九人,则被迁来汉中地区的士族可能会更多。这些汉族移民无疑对汉中地区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形成了常璩所说的汉中郡“州牧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的士人格局。 巴蜀地区,以“三巴(巴郡、巴西郡、巴东郡)”、“三蜀(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为重。巴蜀地区又以巴西郡、蜀郡为首。巴西郡,士人群体“冠冕三巴”。蜀郡,多文学,有学馆;出“西夷”官;大姓极多。出“西夷”官反映了汉以蜀为中心经略“西南夷”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即所谓“各以地比”的施政策略。同时,“三巴”、“三蜀”还存在多文学(三蜀)和“世挺名将”(三巴)的区别。还可注意的是巴西郡与蜀郡相邻,反映了秦汉时西南地区汉人分布的中心性结构。当然,在“三蜀”、“三巴”诸郡中,又可以见一定的士人结构次序。比如,“三巴”地区的巴西郡“冠冕三巴”,巴郡“多人士,世有大官”,位于东部的巴东郡则“人多劲勇,少文学”。《华阳国志》对“三蜀”地区的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各郡都有很高的评价,反映了两汉时期成都平原汉文化的高度发展并呈“面”状展开。 巴蜀地区如上大姓、士女特征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时空条件。从汉族移民史料来观之,巴蜀地区汉族移民不仅早,而且规模较大。蜀地移民最早当在秦代,但秦初期的移民不在成都平原中心区域,而是其边缘地带。史料上,秦人移民巴蜀留下一些地名,如秦水、秦川。《太平寰宇记》卷74《剑南道二》嘉州条谓“秦水在(罗目)县西一百二十里”,《舆地纪胜》卷《成都府路》嘉定府景物上条记“秦水,在峨眉县西南三百余里”,《大明统一志》卷72《嘉定州》等多记峨眉西南之秦水。这些记载均说明秦水之命名即源于秦并巴蜀后“移秦民万家以实蜀中”之秦人,为早期的秦移民,在川西南地区。又,严道之名,《史记》卷71《樗里子甘茂列传》载樗里子秦惠王二十六年(前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严君”,司马贞索隐曰:“严君是爵邑之号,当是封之严道。”《太平御览》卷《州郡部十二》剑南道条记雅州严道时则引《蜀记》曰:“秦灭楚,徙楚严王之族于此,故谓之严道。”临邛汉民亦可为一证,《华阳国志》卷3《蜀志》蜀郡临邛县条记载“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现今发现的秦人移川墓地,有青川郝家坪墓地、荥经曾家沟和古城坪墓地、成都市龙泉驿区墓地,断代多在战国末期,亦多不在蜀地中心区域。 但经一段时间发展后,汉族大姓开始向成都平原中心区域迁徙,有成都近郊一处汉墓门枋上的石刻为证,谓吕氏:“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氏子孙。……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吕氏之后墓在成都,当是迁汶山后又迁至成都的。换个角度看,成都地区两汉室墓、崖墓分布格局亦可作一旁证:西汉时,成都中心地区以竖穴墓为主,边缘地区有室墓但数量规模不大;至东汉末时,成都中心地区代之的是室墓、崖墓,且数量规模较大,竖穴墓虽有但数量规模大大减小。 蜀地汉移民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尽管真实的移民数量已无法得知。从文献上可知秦统一六国前移民入川实为惯例甚至是定制。《史记》卷30《陈胜项籍传》载范增说:“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之。”后有如淳注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知此曾为定制。类似的记载,尚有《尹宙碑》说:“秦并天下,侵暴大族,支判流离,或居三川,或居赵地”。这里的“三川”,概指当时的巴蜀地区。睡虎地秦墓竹简记录了一位父亲要求将儿子强迁往蜀地的边县,并要求其子终身不得离开迁入地,官府似乎未经审讯即同意了这位父亲的要求。葛剑雄推断,官府未经审讯即可同意这位父亲的要求,可见当时此类处罚有法规的支撑并已相当普遍,或是已形成了一套安置“罪犯”移民的制度。作为惯例甚至定制的“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的人口数量是无法考证的,但由两汉巴蜀地区已渐为重要的汉文化区观之,移民的人口规模必然是很庞大的。 除此之外,《汉书》卷30《艺文志》载《尸子》的作者佼曾师从商鞅,及鞅死,佼逃入蜀地;《文献通考》卷26《国用考四》载汉王二年(前年),关中大饥,汉王令百姓“就食蜀汉”;《史记》卷8《高祖本纪》载汉元十一年,“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史记》卷41《袁盎晁错列传》载淮南王作乱时,“迁蜀”;《汉书》卷1《高帝纪》载高帝十年,“六月,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光武五年,“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三国志》卷31《刘二牧传第一》引《英雄记》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武都郡、阴平郡总叙条另载有武都郡、阴平郡东汉末汉民因羌乱南下蜀地。 这些记载中入蜀的群体主要包括逃亡、因罪废迁或罚迁、流民三类。除个别逃亡人群规模较小外,因罪废迁或罚迁及流民的规模当是相当可观的。这些迁入的群体逐渐成为巴蜀地区的主体居民,至汉末时随着这些迁入群体的发展导致了原西南夷群体分布的进一步变化。比较典型的是犍为郡的僰道区域,《华阳国志》卷2《蜀志》犍为郡条僰道县有“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童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的记载,说明东汉时期僰道地区已主要是汉民的分布地。迁入僰道区域的汉民当主要来自成都平原,且主要因成都平原的人口压力所致。据葛剑雄的研究,西汉时成都平原人口密度已在每平方公里人已上,在当时已属于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东汉时,蜀郡辖地大幅缩小,人口却从元始二年(2年)的户增加到永和五年(年)的户,成都平原的人口密度自然比元始时高得多。由此事例亦可知,在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汉族移民除文献记载所见的情况外还有因人口压力造成的人口流动。 与“三蜀”、“三巴”毗邻的宕渠郡、南广郡、朱提郡,有一定数量的大姓士女,但汉族移民的史料较少,大体上当是汉夷杂处的区域。宕渠郡有一定数量的大姓,但该郡主要是板楯蛮的分布区。《通典》卷《边防三》板楯蛮条记载到汉末宕渠板楯蛮迁于汉中杨车阪,称为杨车巴;魏武时又迁至略阳地区,被称为“巴氐”。由此可见,板楯蛮在汉末晋初曾大规模地向《华阳国志》魏兴郡、汉中郡地区迁徙,则宕渠郡在两汉时期主要是板楯蛮的分布区。南广、朱提二郡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口,不过史料不多,后文依据考古材料来说明。其中的朱提郡,《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朱提郡总叙条云:“其民好学,滨犍为,号多人士,为宁州冠冕”,可见该郡在南中地区汉文化发展程度是最高的。 除南广、朱提二郡以外的南中地区有一定数量的大姓、士女,但其人数较前述区域要少得多,其原因在于迁入南中地区的汉族人口较汉中、巴蜀地区要少得多,且汉族迁入时间相对较晚。《史记》卷30《平准书》说“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既然是“募豪民田南夷”以补充租赋,则募民不在少数,该志说“作者数万人”。南夷此不详,或故滇国滇池区域,或故夜郎国中心区域。因与汉通南夷道的语境有关,此次移民可定在南夷道所通之区域。另外,《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晋宁郡初开时,“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来源地不详,但因有“奸豪”的成分,人数当是可观的。 因移入南广、朱提二郡以外的南中地区汉民较少,东汉时,在以建宁郡、晋宁郡为中心的南中地区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地理景观,即汉夷的结合而形成的特殊政治力量结构。《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总叙条有一重要记载:“以夷多刚很,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大姓领部曲之结果之一,本当“汉夷”之融合加剧,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总叙条中说南中地区的的一项记载很有意义,谓晋世时南中的汉人“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由此条记载可知,“南人”与“夷人”在文化上相互包括的程度很深。而且,从这条记载上可看出“夷人”与“南人”关系极紧密,“夷人”可以为“南人”藏匿罪犯,甚至为其复仇。这种情形反映出,汉末晋初南中地区已形成了三种政治力量:“夷人”、“南人”、官府。而在上述例子中,“夷人”、“南人”显然相互依靠共同对抗官府了,《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晋宁郡条云该郡“俗奢豪,难抚御,惟文齐、王阜、景毅、李颙及南郡董和为之防检”的记载对此亦有说明。 两汉并蜀汉对南中地区的治理措施也反映了南中地区的“汉夷杂处”格局。《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总叙条记载到:“李恢卒后,以蜀郡太守犍为张翼为都督。翼持法严,不得殊俗和。夷帅刘胄反,征翼,以马忠为代。”张翼执法严而不考虑“夷”俗,导致“夷人”反判,亦说明此期蜀汉对南中地区的控制是较为有限的。同志所记载到的建安七年(年),赵韪败于刘璋时以庞羲使程畿,畿曰:“郡合部曲,本不为乱,纵有谗谀,要在尽诚,遂怀异志,非所闻也。”亦说明此时对“夷”人的治理主要采用的是依靠部曲力量“以夷治夷”的策略,而部曲则与大姓共生共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建宁郡。尽管该郡有四姓及霍家部曲,但即使是在该郡治县味县也只能采取羁縻之策,其明月社即因“夷晋不奉官”,导致“官与共盟”,说明汉晋间对此区的治理仍采取羁縻之策,边远县更当如此。此外,位于建宁郡东部的伶丘县,其职能是“主獠”,说明在伶丘县东部、南部主要是獠人的分布区,而其北则有一定数量汉人的分布。建宁郡、晋宁郡地区汉民本即数量有限,蜀汉末的战乱导致这些地区的汉民又迁往他处。《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总叙条记晋初“夷愈强盛,破坏郡县,没吏民。会毅疾甚,军连不利。晋民或入交州,或入永昌、牂柯,半亦为夷所困虏。”这些外迁的汉民,当在稍后的历史中融入到“西南夷”中了。 基于以上论述,可判定汉晋时除南广、朱提的南中地区大致上“夷”远多于汉。在这种格局下,只有大姓集中分布的区域会形成汉族的连续分布,边远地区则是“夷”的连续分布。再考虑到“汉系墓”与“夷系墓”的数量关系,可以断定南中地区的汉族分布具有相当的聚居性,但大体上亦有连续分布的趋势,只是数量不多。 余下郡多为基于原“西南夷”集团而设置的郡,这些郡中当是有少量汉人分布的,但或只零星地分布在局部地区(表1、2中有零星大姓或士女分布的郡),或分布并不稳定(武都郡、阴平郡如是,汉末羌乱时晋民尽出入蜀),汉文化的影响也不明显。如涪陵郡、魏兴郡、武都郡、阴平郡、汶山郡、汉嘉郡、越巂郡、越巂郡、江阳郡等,被常璩看成是习俗妖巫的区域,永昌郡、云南郡、梁水郡、兴古郡、平夷郡、夜郎郡、平夷郡、夜郎郡等则是“无文学”的区域。 三、室墓、崖墓墓葬文化所见秦汉西南“汉夷”格局 前两节主要是从史料的角度分析秦汉西南的“汉夷”格局,本节则用考古材料作一对比。本节用以分析秦汉“汉夷”格局的考古材料,主要是石、砖室墓(行文统称“室墓”)和崖墓的分布。童恩正、罗二虎的研究均表明,秦汉石、砖室墓的分布,大体上属于汉族移民或遗民的墓葬,考古报告中常将这种墓形称为“汉系墓”。砖室墓为汉族移民墓葬向来无异议,此不赘述。于崖墓族属方面,存在汉化夷民和汉移民两说,但在汉末时均可看成是汉族墓葬。此外,除其他学者提到的崖墓为汉族墓葬证据外,近年考古发现的两则证据亦值得注意。一则是成都市新都区东汉崖墓HM3墓右门背面有一“石门关”刻字,内容是:“惟自旧忯,段本东州。祖考徕西,乃徙于慈。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此段文字清晰地表明,此段氏家族是从东方迁来的,采用此崖墓形制的墓主确曾为汉族移民。东州在两汉泛指司隶、豫、兖、冀、徐、并六州,或特指青州北海国一带。另一则是中江塔梁子崖墓3号墓的壁画榜题,共有三幅,内容较多此不赘引。这些榜题表明墓主家族是因罪从东迁来的,只是荆文君子宾史无载,迁徙源地不详。换言之,崖墓墓主即使不尽是汉族移民,至少也有一部分汉族移民是采用崖墓形制的。 基于以上室、崖墓墓主族属的认知,在基于罗二虎等石、崖墓分布地及其数量资料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补充近十余年来考古所见室、崖墓的分布及其数量,得出秦汉时期室、崖墓分布演变情况如下: 在室墓分布方面,依据分布地的情况可分期如下:秦及西汉早期,分布地包括今汉源、什邡、万县、巴县、广汉等地;西汉中、晚期,分布地包括今成都、什邡、巫山、昭觉、丰都、江北区、万州、云阳、忠县、赫章、黔西、清镇、平坝、威宁等地;东汉早期,分布地包括今成都、理县、邛崃、巫山、荥经、奉节、江北区、万州、云阳、忠县、赫章、黔西、清镇、平坝、威宁、务川、晋宁、昭通等地;东汉中、晚期,分布地包括今宝兴、成都、达县、大邑、昭觉、绵阳、彭县、郫县、什邡、双流、巫山、西昌、宜宾、大渡口区、丰都、涪陵、合川、简阳、剑阁、万州、武隆、云阳、忠县、安顺、赤水、习水、兴义、兴仁、赫章、金沙、黔西、清镇、平坝、呈贡、大理等地。结合各地室墓数量来看,至汉末时西南地区室墓的分布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密集区,以成都及其周围地区、峡江地区为代表,室墓分布或呈块状,或呈带状,均连续分布且数量较大;另一类为零星区,即密集区以外有室墓分布的地区。需要注意的是,零星区的室墓虽在较大尺度空间上不连续分布,数量亦不多,但在有室墓分布的地区则有多处室墓的发现,如云南地区的今保山、呈贡、大理、昭通地区,贵州地区的安顺、赫章、黔西、兴仁等地。 崖墓在西南地区的出现在西汉晚期,其分布以成都平原沿河流域最为集中,峡江地区亦有较多分布,但始终没有达到滇中、黔中及其南部地区。在分期的层面上,西南地区汉代崖墓的分布可作如下分期:西汉末至东汉早期,分布地在成都平原周围的川中地区;东汉中期,分布地包括川西、川南、川中地区;东汉中晚期,分布地包括四川盆地、峡江、滇东北、黔西北地区,达到崖墓分布最大范围;蜀汉以降至南北朝时期逐渐衰亡,分布地逐渐向川北地区收缩。崖墓在西南地区的出现虽较晚,但其规模却比较庞大,三台郪江崖墓群、乐山市崖墓群、合江县崖墓群、彭山崖墓群发掘的崖墓数量均有数百,其中三台郪江崖墓群发拙崖墓数量达到墓。 以上室、崖墓的分布情况,较《华阳国志》大姓、士女分布及其他史料所见秦汉汉族格局是有一定差异的。特别是在于汉族的主要分布区方面,除基于《华阳国志》所得区域外,巴郡、巴东郡的长江一线,西汉时的室墓主要分布在江州、鱼复地区,至东汉时自江州至鱼复均有大量分布,故可以认为东汉时巴郡、巴东郡长江一线已有大量汉族分布。而从崖墓的分布来看,梓潼郡南角、蜀郡东部、犍为郡北部和西部、广汉郡中部和西部、江阳郡至巴东郡的长江一线西汉时有大量竖穴墓的分布,但东汉时竖穴墓的分布已大大减少,代之的是大量汉系的室墓特别是崖墓的分布,可见该区在东汉时期族群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此外,汉族分布较为零星的夜郎郡地区,在东汉时有一定数量室墓的分布。该区目前考古资料所见西汉并无大规模竖穴墓的报道,但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清镇、平坝、贞丰县、兴仁县有大量竖穴墓的分布,这种格局说明夜郎郡地区在东汉时是典型的“汉夷”交错地区。同时,夜郎郡在东汉时较大规模室墓的分布与竖穴墓的分布均大体相邻(这可能与考古发掘工作进展有关),说明“汉夷”交错的格局是比较明显的(下文有具体考古文化说明之)。 除了墓葬形制反映的不同区域“汉夷”格局外,墓葬所见汉文化特征亦可作为“汉夷”演进态势的一个旁证,现依典型地区叙述如下: 巴蜀地区汉墓所见文化特征包括两期:西汉早期至中晚期,土著文化逐渐消失并融入到汉文化的埋葬制度中;新莽时期至东汉晚期,巴蜀地区汉文化内出现新的区域性特征并逐渐加强,在墓葬随葬品和形制两方面均有明显表现。比如,巴蜀文化中最富特色的“船棺葬”文化,进入西汉以后逐渐消失,代之的是中原地区的木椁葬文化。其中最典型的墓地是重庆巴县冬笋坝墓地和成都什邡城关墓地,都自战国持续至秦汉,所见随葬品文化特征和墓葬形制都表现了秦汉之间的转型特征。 晋宁郡(主要是滇池区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巴蜀地区稍晚,主要在西汉中后期,中原汉墓常见的陶明器有所发现,但其土著文化因素则一直持续到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后,滇文化地方性器物近于绝迹,中原输入的器物占有绝对比例,表明迟至汉末,晋宁郡滇池区域已大部为汉文化所覆盖。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墓地,发拙者将该墓群分为滇文化和汉文化两种类型,其中的汉文化于《昆明羊甫头墓地》卷3专门介绍,西汉末至东汉初20墓,东汉初至东汉中期8墓,共28墓。报道者认为,这些汉墓的主人当是汉族移民,判断特征包括:早期墓葬多大型铜生活用具,多朱提堂狼造,除竖穴土坑墓外发现有墓道;晚期汉墓出现砖室结构,随葬品中多俑及模型器。报道者同时认为,这些人作为统治者,与滇归汉后的“反”、“复反”记载相符,两汉对滇池区域的统治已有如同内地一样的郡县之制而非遥领。但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文化特征上,该区秦汉时期竖穴墓数量和滇文化随葬品都占相当比重。比如,位于古滇国腹地南面的江川地区,近年发布了西汉前期至东汉前期的竖穴墓考古资料,两次发掘均发现其滇文化墓葬规模和随葬品都有不断扩大、丰富的发展趋势,西汉中期后才见汉文化随葬品,滇族传统文化器物一直是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的主体随葬品。这种文化特征反映出,古滇国归汉后其统治阶级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待遇,故而能够持续发展。新近发掘的陆良县薛官堡墓地、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墓地考古材料,都可作此种情形的旁证。 南广郡、朱提郡等地,东汉至晋时期墓葬文化中的汉文化特征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其中的“梁堆墓”已有较多的研究。“梁堆墓”墓主的族属,汪宁生以为即“南中大姓”,实为汉化了的“夷人”,在汉晋文献史料上可与《华阳国志·南中志》之“夷汉”、“夷晋”,《爨宝子碑》(《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之“夷晋”相互佐证。“梁堆墓”的形制可归入室墓一类,故不再另述。不过,“梁堆墓”的墓主并非完全由汉化了的“夷人”组成,年呈贡小松山墓葬出土一件提梁壶,足部有铭文“二千石大徐氏”,按《后汉书·百官志》所列此类人物为太守,当原本汉人。 牂柯地区夜郎郡、平夷郡等地,20世纪70年代就有称为“甲类墓”的汉文化墓葬发掘。在平夷郡,赫章可乐的汉文化墓葬,依据出土铜镜、钱币等推定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中水汉墓的年代则以西汉中期为主,上限可至战国,下限在东汉中期。在夜郎郡,清镇、平坝、安顺一带有汉文化墓葬的发现,集中在黔北、黔西南地区。东汉末年,夜郎故地墓葬所见土著基本消失,其中的赫章可乐墓地,可为分析牂柯地区秦汉“汉夷”格局的典型案例。 赫章可乐经-年、年两次发掘,-年共发掘甲类墓39座,乙类墓座;年发掘甲类墓3座,乙类墓座。按报道者的意见,甲类墓为汉式墓,乙类墓为土著人墓。第一次发掘报道中,见甲类墓文化特征为:出土器物多为兵器,少见妇女用具,极少生产用具,器物见“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字,故判断为军人之墓;出土铁剑、铜壶、铜镜、摇钱树、陶屋、陶水田模型等表明部分墓主当是军队中身份较高者;墓葬形制、葬俗与两汉时期汉族的埋葬习俗基本相同。据上,报道者认为甲类墓当为汉族墓,当是。第二次发掘仅见三座汉墓,且分布地与第一次发掘所见同,故从第一次报道的意见。关于汉墓的时间,第一次发掘报道时,报道者推断其时间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可分战国晚期、西汉初期、西汉晚期三期,第二次发掘的报道者认为汉墓战国晚期这一推断可能有误,但亦同时在其他遗迹中发现“四年”、“建”、“建始”等铭文,亦证明西汉成帝时即有汉族进入可乐地区。 与汉式墓相比,赫章可乐的乙类墓达到座,远多于汉式墓。第二次发掘乙类墓葬的分期,报道者结合测年数据和文化特征,推断为:一期在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二期为战国晚期,三期为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乙类墓在三期时铁器增多,但形制具有地方特色,陶器及其他器物亦未见与汉族墓存在大量文化交流迹象。乙类墓的墓主,第一次发掘报道认为当为“西南夷”中的濮人,因发现有椎髻所用的装饰品和大量农业工具与《汉书·西南夷列传》“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夜郎人特征相符合,也与汉晋传世文献所记僚人“干栏”记载相符。 两类墓主的关系,在文化特征方面,如上所述大量交流的迹象不明显。这种文化格局,报道者认为“汉王朝初进入夜郎地区系‘约为治吏’,未经历武力征战,故不存在地方民族被征剿驱赶事件”。但同时,两类墓主生前当无太大的冲突。在两类墓葬空间分布上,锅落包是两类墓交错最多的墓区,-发掘的两类墓葬中,甲类墓14座,乙类墓21座,甲类墓主要分布在山头西、北两侧,乙类墓主要分布在东、南两侧,南侧有两类墓的交错现象。年的发掘,在锅落包山头南侧亦发现有两类墓的交错现象。按第二次发掘的报告,祖家老包墓区和罗德城地墓区事实上也有两类墓的交错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两类墓的主人当在长时期内是和睦共处的,是一种“汉夷”杂居的真实写照。 如上西南地区文化特征的观察,说明秦汉时期西南地区“汉夷”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一,在时间上,以原蜀国故地为最先,次为滇国故地及夜郎故地,这些地区在东汉末时汉文化的影响已相当明显;其二,在空间上,汉文化的分布地区集中于以上三国故地,次为其周围地区,川西、滇西地区的汉文化影响不大。同时,如上地区在秦汉时代都是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重要前站,是以汉文化的分布不仅与汉文化的传播(比如“西南夷”主动接受汉文化)有关系,与汉民族的迁入也当是有直接关系的。 基于如上材料,综合考虑《华阳国志》大姓士女及其数量,史料所见秦汉汉族移民格局,秦汉西南墓葬汉文化空间特征特别是其中的室墓、崖墓分布,可得汉末西南“汉夷”格局如下: 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巴西郡、梓潼郡、汉中郡所构成的区域,不仅有大量大姓、士女的分布,亦有大量室墓、崖墓的分布,至汉末时为汉族的主要分布区。江阳郡、巴郡、巴东郡地区,汉末有大量的室墓、崖墓的分布,并考虑常璩对原巴郡江州为中心的汉夷格局和后来南浦县“主夷”的记载的话,此三郡亦可划入汉族的主要分布区。于汉族在汉末可能已占极高比例的区域而言,从大姓、士女、室墓、崖墓及其数量的空间分布来看,梓潼郡南角、蜀郡东部、犍为郡北部和西部、广汉郡中部和西部、江阳郡至巴东郡的长江一线所构成的区域当是。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虽无大姓、士女,然为秦汉移民重要区域且本有汉民居住,当以汉族为主。 宕渠郡、巴郡和巴东郡的长江以北,并朱提郡、平夷郡、平乐郡、建宁郡、晋宁郡、夜郎郡地区,有较少数量的大姓、士女数量,秦汉移民较晚且数量规模较小,东汉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室墓、崖墓分布,可以看成是“汉夷”杂处的区域。特别是,故滇国和夜郎国中心区域至东汉时在墓葬方面仍然表现为“夷”墓与汉墓杂处且夷墓数量较多的格局,说明故滇国和夜郎国中心区域处于“汉夷”杂处的状态中,其边远地区当是“夷”多于汉了。 《华阳国志》余下区域,多只有局部且数量不多的大姓、士女、室墓、崖墓的分布,秦汉移民记载极少,当是以“夷”为主的区域。 (本文原刊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已删去原有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孙俊武友德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ls/2224.html
- 上一篇文章: 五一来罗定玩,29个罗定经典景点推介,
- 下一篇文章: 设计界哈佛罗德岛艺术学院教授亲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