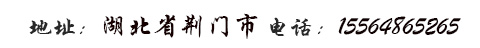19世纪以来,波罗的海的贸易网络,是从何
|
19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关于中世纪前期(5—11世纪)欧洲社会文明历程的发展轨迹多有争议。传统观点认为,西欧社会此时正笼罩于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漫长阴影中,8—9世纪才与罗马传统彻底“断裂”。如皮朗指出,法兰克时期欧洲经济生活逐步走向低谷,金银及商品贬值,商业几乎销声匿迹,完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占据统治地位。 对此持异议者则提出欧洲社会缓慢变革的长时段“转型论”。如奥地利史学家多普施认为,罗马帝国崩塌后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经济体系仍有所保留,欧洲大部分贸易活动还在沿着罗马传统路线进行。在欧洲北部,弗里斯兰农商和维京海盗商人就扮演着早期媒介的角色。 不过学界长期聚焦于贸易参与者的具体活动,反而忽视了其贸易行为连带地区(作为经济、社会或文化单元)的通联效应,即北欧的区域一体化历程。 而且就贸易行为而言,此时的北欧贸易尚不能归于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解释范畴,交易动机多是基于早期地理分工的自然需求(以生存和财富荣耀为目的)。从这两方面来讲,地理要素的特殊作用理应在此时的远程贸易研究中得到优先强调。 时间和空间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基本要素。如果说时间阈值提供的是历史发展的线性背景,那么空间(即地理环境)则左右着人类文明行进的方向与特征。近代历史学家几乎未考虑作为人类活动舞台和场所的地理环境,通常将时间与空间割裂。 对地理因素与人类环境的重视、对地理学功用的突显多依赖于非历史学家,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家。正如19世纪英国学者麦金德的观察:“地理学的主要职能应是探索人类在社会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局部发生变化的环境中的作用,人们在考虑相互作用之前,必须对起相互作用的因素(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分析。 这些因素之一就是变化着的环境”。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裨助年鉴学派实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学科整合。徐浩和侯新建认为,费弗尔首先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叙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各种实践活动性质的影响,分析人的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将社会史与自然史统一于人的实践当中。 布洛赫则指出,对于支配着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最终只有通过对整个人类环境的认识才能得到理解。何兆武和陈启能认为,布罗代尔创建长时段历史观,将地理学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助于发现缓慢运动事物的结构———这种长期存在、相对稳定的结构限制着人类历史变化的幅度。 在古代,地理环境在欧洲经济增长中施加的影响特别强烈(但并非起决定作用):它是欧洲社会更大范围分工和交换的基础,刺激商业和手工业复兴及农耕文明的再繁荣,促进远程贸易的发展。布罗代尔以地中海为研究对象,阐述并实践了其长时段理论。 年,瑞典、挪威、丹麦和芬兰成立“北欧学协会”寻求文化领域的深层合作;自年起,北欧各国学者定期召开“维京学会议”,鼓励新视野,传播新思想,以弥补英语学界的欠缺;年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又轮流召开以“维京时代”为主题的研讨会,议题覆盖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各领域;年,在悉尼召开的“萨迦国际研讨会”首次将早期文明研究推向全球。 北欧区域贸易网络初显。在中世纪早期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低地农商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商人的海外活动铺设了北欧贸易的孔道。弗里斯兰地处莱茵河口三角洲,其居民因土地有限而背井离乡,只得寻求贸易以维持生计。尽管法兰克人侵扰不断,但弗里斯兰社会还是通过抗争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 加洛林王朝对弗里斯兰人采取绥靖政策,亚琛宫廷甚至还成为弗里斯兰商人的重要主顾。八百年左右,弗里斯兰人开始将本地纺织品运至外域,其商业据点遍布西德意志的主要城镇(如美因茨、沃尔姆斯等)。弗里斯兰拥有当时北欧最大的海运港口———杜尔施泰德、蒂埃尔和科恩托维克,凭此与英格兰、冰岛、挪威和丹麦群岛互通有无。 弗里斯兰人的核心贸易区在低地北部、德意志北部、施勒苏益格地峡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贸易网络的辐射外围是以杜尔施泰德为中心向西经加莱或乌特勒支渡英吉利海峡到达哈姆维克(今南安普顿)和伦敦,再西行绕过兰兹角或北上绕过苏格兰北端进入爱尔兰海;向南进入高卢、勃艮第的法兰克王国,经塞纳河到达巴黎的圣丹尼斯集市; 向东溯埃德河和特瑞纳河而上,到达霍利希施泰特,再走17公里陆路到达海泽比;向北可达丹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里伯,然后绕过日德兰半岛,穿过丹麦群岛到达海泽比。波罗的海的交易中心施勒斯维克和比尔加很早就与杜尔施泰德建立贸易联系,近代在丹麦发现的大量当时铸币几乎都是以杜尔施泰德币为模板。 11世纪里,弗里斯兰商人在瑞典的锡格蒂纳和英格兰的伦敦等地建起一系列商业“基尔特”。 弗里斯兰商人群体衰落后,其南邻佛兰德商人继之成为北海南岸最具活力的贸易群体,他们的主要贸易对象是英格兰。佛兰德商人从魏桑和布鲁日出发,在伦敦建起早期“汉萨”组织。两地之间的商品、信息交流极为密切:据说年佛兰德伯爵好人查理的死讯在次日清晨就传到伦敦。 佛兰德商人输往英格兰的商品主要是当地呢绒和法国红酒,运回的则是锡、铅、兽皮和皮革等原料。佛兰德诸城中,尤以摩泽尔河流域(如布鲁日、于伊、列日、尼韦勒和迪南特等城)的商人最为强盛。 他们将莱茵兰的红酒、金属制品和宝石,美因茨的甲胄,雷根斯堡甚至君士坦丁堡的奢侈品转运至英格兰;将德意志塔廷的陶罐经莱茵河三角洲输往瑞典的中南部、挪威和拉多加湖畔。 斯堪的纳维亚人中,挪威水手在8世纪时活跃于北海,面向西方从事劫掠贸易。据英格兰的《贸易与商业年鉴》证实,汉萨商人出现前,挪威人的船只每年都会到达英格兰东海岸的格林斯比、波士顿和金斯林恩等港口。 近代考古学家已从上述地区复原出维京人的殖民遗迹。挪威人还活跃于布列斯托海峡至威尔士沿岸的广阔地区,一度将爱尔兰海变作他们的“挪威内湖”。考古学家在爱尔兰里弗河口的都柏林旧港遗址中发现了大量9世纪的舶来品,如英格兰的陶器、波罗的海的琥珀和东方的丝绸等。 15世纪的《阿尔斯特编年史》还记录了10—11世纪时都柏林维京商人交易奴隶、马匹、蜂蜡和谷物的情况。9世纪末挪威北部哈罗加兰德的部落首领奥塔尔曾出访威塞克斯宫廷,觐见英格兰国王阿尔弗雷德。奥塔尔声称他曾沿盎格鲁-撒克逊、弗里斯兰、挪威、瑞典和斯拉夫海岸巡游。 挪威的南邻丹麦人致力于征服不列颠东海岸,鼎盛时期的丹麦国王克努特(—年)还曾一统丹麦、挪威和英格兰。据19世纪末的英国历史学家考证,泰晤士河口的谢佩、希尔内斯和舒伯里内斯,英格兰北部的斯哥希内斯、格林斯比、惠特比以及自布里斯托海峡至威尔士沿岸许多城镇的名字可能都源自古诺斯语。Bugge还从语源学考证了索斯沃克城的起源。 他认为该城的“市民集会”传统就与克努特统治有关。丹麦人在英格兰掠夺的银币大部分直接用于海外消费,如在德比和拉格比购置地产,或用来维持与欧洲大陆的贸易———他们频繁前往不莱梅、乌特勒支、科隆、佛兰德和诺曼底等地,从波罗的海南岸转运鱼干、毛皮、皮革、盐、黄油和其他产品。 北海沿岸的卑尔根和特伦德海姆及斯卡格拉克海峡的奥斯陆和滕斯贝格逐渐发展成维京人的转运中心。瑞典在当时相对富足,其土地较为肥沃,盛产金银、战马、海狸皮和貂皮等物。瑞典人主要向东拓展,从事劫掠贸易或加入雇佣军(成为罗斯王公的亲兵)。他们在斯拉夫地区被称为瓦良格人,建起早期罗斯国家。 结语 他们经常前往拜占庭和黎凡特市场,以毛皮、奴隶、猎鹰、蜂蜜和蜂蜡交换拜占庭或哈里发王国的银器。据《往年纪事译注》记载,年以前的诺夫哥罗德就已出现瓦良格人的自治商会组织,其活动中心可能就位于市中心的波罗莫尼宫。正是从维京时代起,横跨北海—波罗的海的贸易网络才开始日渐明晰。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ls/10819.html
- 上一篇文章: 北欧最能打的瑞典,帮助东斯拉夫人建国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