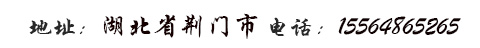西塞罗是欧洲修辞学重要的导师,他的巨大影
|
引言 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知道,“由自然出发”并不存在所有权。克吕西普对此并不赞同,难道对于财产的权利只是一种暂时的要求?他没有责骂富人:“正如一个人走入剧院,占了一个位置,把其他后来的人都挤掉了,在这个意义上,原本所有人共享的东西,现在只由他独享:这就是富人。 因为在他们事先占有了公共的东西之后,他们通过抢先夺取而将这些变为自己的财产。如果每个人仅索取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东西,而把其他人需要的留给他人,哪里还有富人,哪里还有穷人呢?”然而,帕奈提奥斯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即心理学式的对财产的辩护。对他来说,人类文化的历史中的一切,都开始于我们的祖先想要保护他们的财产。从这里发展出城邦的保护区。相反,试图彻底清除和重新分配传留下来的财产的人,是有罪的,帕奈提奥斯的这一论证,可能是为了反对格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 私有财产法是一种习惯法,无论是先来的人还是前来争夺的人,都应该将其维持下去。这种论证并不特别有说服力。如何为罗马人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量土地掠夺辩护呢?希腊人、色雷斯人、帕伽蒙人、叙利亚人等等,他们的土地以前并不属于罗马。为什么在罗马城里适用的,对于那些罗马城之外的罗马人就不适用呢?中期的和更晚的斯多亚主义者为财产权奠基,还缺少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对于后来的自由主义是决定性的,它就是“成就”的概念! 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如果财产属于我,那是因为我基于劳动成就获得了它(或者基于我祖先的劳动成就)。财产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能力证明自己的合理性。有能力者应该获得并保有他应得的东西。然而,罗马人和古希腊人一样都缺少成就的概念。公民并不通过劳动获取什么,妇女和奴隶也是。能力是人们在经过训练的伦理交往中自己培养的,而不是借助劳动工具。 在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看来,适用于财产概念的,同样适用于政治。一切都应该如其所是地维持下去。少数强大的领导者应该引领生活在罗马帝国中的大众,这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一个。年轻的罗马人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在罗德岛的波希多尼的哲学学校学习的正是这些。西塞罗是贵族家庭的后代,之前在罗马和希腊学习。几乎所有我们关于帕奈提奥斯和波赛东尼奥的信息都要归功于他的记载。西塞罗首先致力于哲学研究将近20年,撰写了大量作品,并将许多希腊文书籍翻译成拉丁文。 作为优雅的文体学家和修辞学家,西塞罗属于罗马最为优秀的人物,随后他开始了变幻无常的从政经历,先成为执行长官,之后陷入生命危险。他被恺撒的后继者所迫害,并于公元前43年自尽。西塞罗将成为欧洲修辞学最重要的导师。他的巨大影响在于简明扼要的文风,他精通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来定义。此外,他将智慧与说服力联系在一起。因为智慧若没有雄辩是没有用的,而雄辩没有智慧则会造成许多灾祸。 西塞罗的哲学接近斯多亚派,但也有很多柏拉图式的思考。这给他带来“折中主义者”的名声,即在自己不参与的情况下从所有东西中挑选出合适的。西塞罗对罗马的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更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学。他让罗马人了解,人类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能动的。他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倡导自我责任。同时,他接续了柏拉图关于伦理学与城邦哲学的思考。西塞罗关于城邦(《论共和国》)和法律的著作(《论法律》)讨论的是《理想国》和《法律篇》的中心思想。然而,他的城邦理论比柏拉图更为现代。 对于西塞罗来说,城邦是基于权利约定与利益共同体而建立的。城邦的基础是,在正义和有益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他的政治哲学的终点不是梦想中的理想国或者想象出来的马格尼西亚,而是罗马共和国,正如之前的帕奈提奥斯,他以同样的热忱宣称,罗马的宪法是所有宪法中最好的。怀疑天命中期和年轻的斯多亚派在很长时间内费尽心思地为帝国的现状辩护。而这也使得斯多亚派成了真正的罗马官方哲学。为此,对斯多亚主义做出重大改变也是有必要的。 人们抛弃了普遍原则,将伦理学几乎仅仅移到私人领域。我自己认为正确和可敬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我的政治行为!对事物的基本看法与特定情况下的行为无须在逻辑与实际上保持一致。罗马的斯多亚主义者具有异常灵活的原则。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适应政治生活。同样进入罗马的伊壁鸠鲁学派则仅仅扮演了一个很小的角色。在斯多亚主义者看来,伊壁鸠鲁主义是大众哲学的快餐,但这一看法肯定是不准确的。毕竟在恺撒身边,更多的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他自己也可能跟伊壁鸠鲁的学说很接近。同样,像维吉尔和贺拉斯这样的诗人也钟情于伊壁鸠鲁主义哲学。 它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伽达拉的菲罗德谟斯,他当时从现在的约旦来到罗马。他的作品被认为简单易懂。菲罗德谟斯撰写哲学和文学的文本为伊壁鸠鲁辩护。留传下来的主要是诗歌集,其中部分带有色情的内容。菲罗德谟斯为受到抨击的伊壁鸠鲁主义做了详细的辩护,这不是偶然事件,因为其他哲学学派,尤其是斯多亚主义最为反对伊壁鸠鲁的学说。 还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需要辩护。把人类看作一种神性天命的目标以及把罗马帝国理解为历史理所应当的终结,伊壁鸠鲁学派与此观点相距甚远。而著名伊壁鸠鲁主义者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5—前55)的诗作《物性论》则发展出一种特别现代的自然演化论图景。据此,在人类诞生之前,我们的世界已经持续经历着动植物的来回往复了。没有什么是长久存在的。“时间改变整个宇宙,地球上遍布着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以至于一种状态不可能再生成它曾经所是的样子,而是要变成它之前不可能的样子。” 卢克莱修不讨论那个只服务于人类的自然母亲,而是讨论“自然继母”。对卢克莱修来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财产和金子不是天命有意创造出来的元素,而是分裂、不幸、争执的源头。一种对自然与文化的考察,不把现状视为永恒和终极的,并将财产看作有害的东西,这不适合作为官方哲学。它甚至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清醒地保持对罗马的世界秩序的怀疑。甚至如吕齐乌斯·安涅·塞涅卡(公元前1—65)这样著名的斯多亚主义者,都没办法摆脱对这个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的伊壁鸠鲁式怀疑。 也许这位在罗马飞黄腾达的富有的西班牙人,总的来说是被阅读最多的斯多亚主义者。他信奉心境平和和泰然自若的理想,为理性对于激情的优先地位辩护,是人类平等的坚定支持者,慎重地批判奴隶制度。命运将重担加之于他,使他成为国师,培养罗马皇帝中最残忍和疯狂的尼禄,这应该对塞涅卡泰然自若的能力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塞涅卡被他的学生所迫而自杀之前,在诸多信件中,没有忘记对斯多亚主义的自然—神式的天命进行立场鲜明的批判。 在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渗透将世界尽数摧毁之前,一切本应该是更好的,对芝诺和克吕西普来说是如此,对塞涅卡来说也是如此:“你说什么?哲学教会人类使用钥匙和门闩?那除了给贪婪的人以暗示,还有什么别的?哲学为处于巨大危险之下的居民建造了高大的建筑?依靠偶然措施来保护自己,在没有技术和困难的条件下发现自然住处,这还不够吗?相信我,在建筑师和泥水匠之前的时代是幸福的。” 塞涅卡沉溺于一种对技术和文化进步的深深的悲观主义中,而非通常的历史乐观主义——一千七百年之后,一位来自日内瓦的钟表匠之子,卢梭,以同样的态度在哲学中引起了轰动。尼禄狂暴地迫害了越来越多重要的斯多亚主义者之后,曾经的官方意识形态很快失去了影响力。晚期的斯多亚主义者,例如来自今日土耳其中部弗里吉亚地区被释放的奴隶爱比克泰德(约50—约),尽管使斯多亚伦理学更为精进,但在政治上持消极态度。 最后一位伟大的斯多亚主义者,皇帝马可·奥勒留(—),他用古希腊语撰写的《沉思录》,并不面向广泛的大众,而仅为自己。这些在今天各种格言集中都不会缺席的精炼语句,劝导人们在巨大的世界整体面前保持谦虚、恭敬和泰然自若。皇帝对伊壁鸠鲁格言做的注解几乎与原文相混淆,考虑到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百年的敌对,这看起来有些讽刺。“幸福,意味着拥有好的品格”;“一根苦的黄瓜?把它扔掉吧!路上的荆棘?避开它吧!就这样。 不要再问:世界上为什么存在这样的东西?”;“人们在乡村的田野、海岸边、山中寻求隐居。然而,这种愿望产生于一种狭隘的观点!只要你想要,任何时候你都能做到,抽身返回你自己。没有任何比人类灵魂更安静而不受干扰的避身之处。”关于永恒的智慧:“那些你时常沉思的想法完全是你的意向。”斯多亚主义的思想保留下来,经历了一条多么漫长的路!从一种严格、无情的教条出发,要求在一种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自我完善,到技术与政治上罗马的统治使命,直到马可·奥勒留的自我沉思中寂静的忧郁! 结语 一开始,斯多亚主义是一种社会纲领,一个改变世界的计划。到最后,它成了一种心理上敏锐与智慧的私人哲学,不再洞悉统治使命,“谁能够改变人们的基本原则呢?”伴随着这句机敏的话的,一定是一种谨慎的畏惧。作为皇帝,马可·奥勒留必须为自尼禄以来对于基督教最为残忍的迫害负责!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dechenga.com/ldcjt/11161.html
- 上一篇文章: 明日方舟浮士德简直堪称劳动模范,玩家他见
- 下一篇文章: 美国注册猎人最多的州排名加州最少